谢阁老心下一惊,抬起眼皮瞄了一下颜凝,只见她低着头,看似正在专心吃饭,嘴角却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
谢景修恨她胆大妄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轻薄调戏自己,便合拢双腿,试图夹住她作恶的小脚。
可是捣蛋的颜凝被他夹住了脚之后,脚趾扭来动去,刮得他大腿内侧嫩肉瘙痒,足尖时不时碰触到阳物,逗得那东西饥渴难耐,坚持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松开了腿。
“今日这道红烧肉茄不错,茄子里的肉吃上去像真肉,一点也觉不出是豆腐干滥竽充数的西贝货。”
颜凝突兀地说了一句,藏在桌子底下的小脚已经结结实实踩上了公爹胯下“茄子”。
“额……”
谢景修自然听出她在含沙射影说自己坏话,胸中恼怒非常,碍着外人在又不能把她怎样,胯间肉茎则被她灵巧小足踩得舒爽惬意,高高翘起头来,害得他不得不往再前坐一点,免得她穿着小白袜做坏事的脚脚被人察觉了。
泉林姨母还在柔声细语地讨好姐夫,颜凝就把气都撒在公爹胯间,变着方子不厌其烦地磨弄那根阳物,把它踩得快活至极,前端开始渗出精水。
而谢景修强忍着性器上传来的延绵快感,面上看似一片平静,胸口早已心潮澎湃,快意难忍,却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吃饭喝汤,时不时还得回答泉林一两句,简直比上刑还惨。
越是在人前做这种偷偷摸摸的坏事,越是羞耻刺激,谢景修感觉被颜凝踩弄的肉茎舒服得上了天,全身的皮肤都兴奋得一阵一阵地颤栗,到后来完全听不进边上的泉林喋喋不休在说些什么。
颜凝已经可以从他微蹙的眉眼中找到唯有她一人熟悉的欲火了,她原先是想对公爹恶作剧撒气,弄久了自己也开始难受,饭都吃得心不在焉。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胯间的快感已经开始让他感到战栗,这么忍着难保不会露馅。
所以谢阁老不得不三口并作两口把饭吃完,放下碗筷擦了嘴,手伸到桌子底下捏了一下颜凝的脚丫。
随后用宽袖挡在身前从位子上站起身,冷冷说道:“吃个斋饭都没得清静,我去走一圈消消食,你们慢用。”
泉林脸色一僵,尴尬又难过,恋恋不舍地目送姐夫大步离开。
谢绥侧头看颜凝,在桌子底下轻轻撞了一下她的腿,颜凝知道谢绥是让自己去哄哄生气的公爹,可谢小姐不知道的是,她父亲之所以生气一大半原因是因为被儿媳调戏了。
不过颜凝还是找了个借口离席,远远地跟着公爹,一等到四周无人的时候,就抓紧机会把他掳走,揽着他翻墙躲到了寺庙外的林子里。
孟错看是颜凝,很机灵地让其他侍卫止步,不要再跟上去。
一放下公爹,颜凝就环住他脖子挂在他身上索吻,“爹爹,难受,亲亲我罢。”
“你还好意思说!”谢景修嫌弃地推开她的小脸,愤愤道:“关我什么事,你要找我的茬?还说什么西贝货,西贝货你还要什么亲亲。”
颜凝忍着笑抱住他撒娇:“是我错了,不是西贝货,是金刚杵。爹爹爹,您难受不难受?要不要我……我……我点的火,我来灭了它吧。”
“人来人往的,怎么灭火。”谢景修有一瞬犹豫,说话的语气也带着挣扎和不确定。
“爹爹亲我一下,我带您去没人的地方。”
于是谢阁老就勉为其难亲了得意的小颜凝一下,被她用轻功带到陡峭山坡上一处凹陷的小洞,确实没有人能来,因为太抖,没功夫上不来。
时间紧迫,颜凝都没有再去征求谢景修的同意,就解开他裤子蹲下身来把东西含进嘴里舔弄起来,几下之后就把那物吮得亢奋濡湿。
谢景修虽然被她含得舒爽,但想起她刚才说难受,心里又舍不得,不愿意只有自己一人快活。
他把她从地上拉起来,撩起她的裙子,把手探入她下阴:“你是不是上次夜里在花园玩得上瘾了?不知羞!转过身去,让我从后面进去!”
噫,公爹对自己真是越来越随便了,一点也没当初视若珍宝的爱惜。
颜凝撇撇嘴,转身手撑着山壁撅起屁股。
谢景修脱掉她裤子一摸,下阴滑腻腻的已经潮了,在她雪臀上轻轻拍了一巴掌斥道:“动不动就湿,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额……”
锤死锤死!
颜凝为了快活,强自压下心中愤怒,扭了扭屁股催促公爹。
谢景修轻笑一声,手指探入穴中揉按片刻,将蜜穴弄松了便扶着肉茎挤入其中,遂了小美人的意。
他一边挺腰肏弄颜凝,一边感叹自己自从上了她这条贼船之后,就一条道走到黑,什么荒唐淫乱的事都干了,来寺里上个香都要和她在林子里淫交一番,还心甘情愿沉浸其中,彻底回不了头了。
肉茎狠狠碾过阴内花芯,颜凝被公爹入得酥麻酸爽,这里没人迹。
干脆无所顾忌地浪吟起来:“爹爹……啊……好厉害……嗯……嗯……爹爹给我……”
可最初的快意她尚能承受,时间久了,谢景修反复在花芯上冲撞,却渐渐让她受不住了。
他粗壮坚硬的性器对着骚芯研磨碾压,狠扎猛刺,把缠绵柔媚的穴肉捅得艳红烂熟,肉壁汁水泛滥,花芯又酸又软,主动蠕动挤压着肉茎,绞结裹紧,化身密密麻麻的小口对它吮吸不休。
阴道内的肉壁被折磨得欲仙欲死,哆哆嗦嗦地不断吐出爱液,从穴口潺潺溢出。
下身相交之处已经开始发出叽里咕噜的淫靡水声,而被爱液包裹着的肉茎抽出时在日光下反射出晶莹水光。
里面被顶得太舒服,颜凝的浪吟慢慢变成了啜泣。
在光天化日之下林间野合,交媾之时花阴内被摩擦,花芯被顶刺,花芽被撞击,每一处的感觉都似乎比平时更羞耻更激烈,每一下进出都让她身体不住地颤抖,脑中一片空白,穴儿不断收缩,很快就迎来了高潮,哭叫着夹紧腿,霸道的快感从阴内窜上头顶,紧绷着身体眼前发白,失声高吟。
谢景修被她夹得激爽,颜凝泄身他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加快抽送好速战速决。
无休无止的剧烈快感让颜凝感觉自己简直要被公爹弄死了,嘴里不断胡乱哭喊:“不要了……爹爹……不要……嗯……啊……不行……嗯……”
本来无视她的谢景修,弄了几百下看宝贝儿媳一边摇头一边哭到嗓子嘶哑,终于停下皱眉问她:“你要不要紧?真的不行了?要是在外面和上次一样昏过去可不好办。”
可这中途一停,颜凝花阴又万蚁噬心般麻痒起来,她已被快感冲刷得神志模糊,又扭动腰肢催促道:“爹爹……别停……”
然而谢景修再一动,她又哭起来,娇声呼喊:“不要……求爹爹……啊……真的不要了……”
搞得某人额头青筋狂跳,耐着性子把她转过身来抬起一条腿从正面入她,强压下自己一肚子狂风骤雨的急切,轻轻款款,缓送慢抽。
“这样好些吗?我慢一点。”
可颜凝还是不断摇头,咬着下唇极力忍耐,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忍耐体内麻痒,还是在忍耐快感的冲击。
谢景修无奈叹气,他自己也在正爽快的时候,要停下是万万不能的,只想放开手脚发狠地入她。
于是他低头吻住颜凝,封住她嘴里颠三倒四的哭闹,舔吮着她的丁香小舌,下身再次快速冲击。
最后下狠心又疾疾出入了百来次,在蜜穴再一次痉挛着猛地夹住肉茎时,灭顶的快感从谢景修下阴爆发,席卷他的身体,灼烧他的大脑,而颜凝也浑身发抖双腿打颤,双瞳涣散地软倒在他怀里。
他照例及时抽回性器射在外面,抱住虚脱的儿媳亲吻抚慰,给她擦干净腿间,帮她穿好裤子整理衣裙,抹去了颜凝的泪痕。
两人稍稍喘了口气,对刚才的冲动荒唐都有些不好意思,又甜蜜温暖,相视而笑,满腔爱意尽在不言之中。
没想到的是,他们回去泉林姨母还没有走,望眼欲穿地等着姐夫回来,谢绥看到父亲一脸黑,暗自幸灾乐祸,带着笑意别开脸。
可是颜凝不想再装了,看了看对他们同行而来充满疑问的泉林姨母,直接握住了公爹的手,警惕而郑重地对她说:“阁老与我已有婚约,姨母以后还是稍稍避个嫌罢。”
“咳咳……”谢景修突然干咳起来,忍着笑低下头去。
泉林看到他嘴角弯弯,一只手被颜凝放肆地捏在手心也由着她去,就明白颜凝说的是真的,胸中如遭重锤,一时呆怔无措。
正尴尬着,颜凝眼角扫到一个知客僧在不远处看着他们,面孔瞧着似乎在哪儿见过,再看他眼神有些古怪,突然想起来这不是从船上把公爹推下水的那个船夫么?
她本能地把谢景修拉到自己身后,盯着那人神情警戒,像是炸了毛的猫。
谢景修也已经看到那个僧人,安抚地拍了拍颜凝肩膀。
只见对方朝他双手合十行了个礼便转身离去,并没有要再次袭击他。
“那人不是说要收监问斩吗?”颜凝回头问他。
谢景修摇摇头:“他父亲是个铮臣,受诬陷入狱,又被人做手脚害死,家里只有他一根独苗。
我向刑部求了个情,没有计较他的事情。他和你是一样的。”
最后这句把颜凝听得心里一酸,也就是说这人的父亲张迁和自己的父亲颜霁都是因为弹劾曹鷃被冤死的,谢景修当时在大理寺,他没有帮他们翻案,或许是不能,或许是不敢,他心里是有愧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若当时您一时冲动,也不过是让人家手上多一条人命罢了。”颜凝捏了捏谢景修的手心,温声安慰道。
爹爹看上去凶巴巴地,野心又大心机又深,原来也有这样心慈的时候。
颜凝对公爹莞尔一笑,朝伤心欲绝的泉林默默看了一眼,就把心上人给拽走了。
回去的时候谢绥在马车里大肆称赞颜凝的胆气,对她独占自己父亲的决心和气势各种揶揄调笑。
“泉林姨母其实与我家并不亲近,我从外祖家亲戚那里听说她从很久之前就对父亲芳心暗许,一直想着能嫁给他做续弦。
所以家里给她安排亲事她一概不答应,从十多岁的少女拖到现在快三十了,还没成亲呢。”
“那爹爹呢?人家姑娘那么喜欢他,他一丁点也没这个意思吗?”颜凝酸溜溜地明知故问。
谢绥轻笑着摇摇头:“你说呢?知道还问。父亲这人眼高于顶,泉林姨母家里最大的才到六品员外郎。
要不是碍着是母亲娘家亲戚,他连话都不会与她说一句。
即便如此,这位姨母上我家来也常吃闭门羹,父亲从来不见她,她送的东西也一概退回,不留半点情面。
今天要不是我,哈哈哈,他才不会容许她坐他边上吃饭呢。”
“哼,能和他吃饭很了不起么,就他官大,我还不稀罕呢。”
“你真不稀罕?那我去告诉他,让他别缠着你让你为难。”
“我随便说说,你别告诉他。”
颜凝才假模假样傲了一瞬就怂了,太没用,把谢绥笑得前俯后仰。
“官做大了,结交什么人说什么话都要加倍小心,对方是痴恋他的女子,他当然更加得离得远远的啦,否则定要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的。”谢绥替父亲解释道。
睡儿媳妇他也不怕别人做文章,都是借口,颜凝心想。
不过公爹长得太好看,会有人恋慕他不足为怪,幸好他喜欢的是自己。
回到谢府后,颜凝因为白天调皮捣蛋轻薄公爹的事,被谢景修狠狠地罚了一顿,又哭得她死去活来,最后再也不敢多提一句泉林,精疲力尽蜷在公爹怀里睡了过去。
谢衡回了一苇小筑后,颜凝的东西则被陆陆续续搬去了匪石院边上的新院子。
全家人都渐渐知道二少爷夫妇已经和离,二少奶奶不再是谢家的人。
可颜凝仍旧光明正大留宿在公爹处,下人不敢说什么,谢衡谢绥三缄其口,余姨娘不敢置喙,只有谢慎觉得父亲与弟媳离经叛道,不知廉耻。
既然已经和离,就该早早回娘家才是,没名没分地留在公爹房里算什么。
颜凝对此毫无察觉,日日夜夜与前任的公爹红烛帐暖,被翻红浪。
在听到翰林院同僚与他提起曾在光华寺见到谢阁老带着女儿儿媳上香后,谢慎实在忍无可忍,父亲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不顾脸面,把儿媳妇公然带出门去,这是要毁了谢家百年清誉啊。
他不敢去找谢景修,就让妻子江氏把颜凝请来长房院子小坐,无论如何也要试着把她劝走。
嫁到谢家那么久,颜凝与大伯谢慎说过的话大约不超过十句,谢景修不把人召集到一起,他们甚至都见不到彼此。
所以她对谢慎夫妇找她十分紧张,坐在他们屋里也非常拘谨。
“弟妹……额……渚渊,听说你与二弟已经和离,我这弟弟荒唐固执,是我这做兄长的管教无方,害你受苦了。”
说话的是谢慎,江氏坐在一旁并不出声,颜凝已经隐隐猜到对方大约是冲着她和谢景修的事来的,等了那么久,终于有个正常人要指着她的鼻子羞辱她了。
“没有没有,二少爷待我挺好的,人各有志而已。”
虽然对着一脸“我已经准备好迎接狂风暴雨”的颜凝很难开口,但要说的总得说。
谢慎清了清嗓子,看着桌上杯子说道:“二弟负了你,是他不对。只是不知弟妹……渚渊准备什么时候搬回王府去?”
颜凝沉默半晌,也低头看着杯子。
“我不回去。”
“额……”
江氏讶异地看了看颜凝,又看了看拧起眉毛的丈夫,想打圆场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已经不是谢家的人了,无名无分住在此处,于理不合,有碍风化。”
谢慎自觉这话已经说的很重了,可是颜凝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分毫不让。
“我不走,谢家做主的是爹爹,要我走,除非他开口。”
一提父亲谢慎就更上火了,怒瞪着茶杯寒声道:“你与父亲私……私……私下往来,他当然不会要你走。
可是他沉迷女色不顾名声,别的人却不能装聋作哑。
就算和离了,你与他也是翁媳,他不可能娶你,难道你想一辈子这样没名没分地住在他院子里?
又当不了妻子,又不算侍妾,甚至连外室都不是,你一个妇道人家,就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吗?”
背负着背德罪恶感的颜凝,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有个正常人,会像天下所有人那样,骂她不要脸,骂她扒灰私通公爹,让她为自己的任性付出稍许代价,可真到了这一刻,她还是受不住,眼泪像断了线的珠串,停不下来。
“我的事不要你管!”她倔强道。
“谁要管你的事,你害得谢家全家人跟着你丢脸,凭什么?
就凭你是荣亲王的远亲?凭你算半个皇亲?就可以不顾廉耻,由着性子乱来,让不相干的人和你一起蒙羞?”
谢慎越说越大声,院子里的下人们都听见他发火,江氏从来没看到过丈夫发这么大脾气,吓得连劝都不敢劝一声。
道理在谢慎那边,颜凝一句话都反驳不了,确实是她任性自私连累了旁人,对方不是荣亲王,不是皇上,更不是谢景修,她的眼泪毫无用处。
她从位子上倏然站起,面色惨白如纸,低着头谁也不敢看,自己举帕子擦了擦泪水,负气说道:“你想赶我走,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反正让我自己走是万万不能的。别说你,就算是爹爹要赶我,我也不会走的!”
说完也不理谢慎还要再骂什么,转身淌着泪急急地走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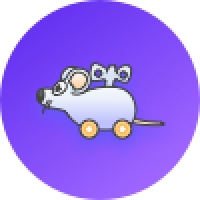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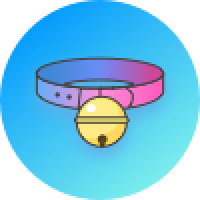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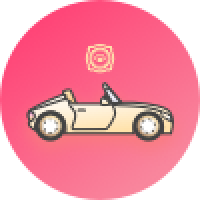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