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向孤山去未归,片云竹雁与心期。
谢景修千里迢迢来到塞北,先在大同边关以巡抚之职安抚战后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关内四处寻访颜凝无果后,又出关走遍当初与北狄交战的大小战场,摸清了关外各个异族部落,在塞外从寒秋霜结一直游荡到暖春绿荣。
草原大漠旷无边际,整个冬季入眼尽是满目悲凉。
他有时心灰意冷,有时又心存侥幸,时常一脸落寞对着茫茫大漠孤鸿落日吹笛寄哀思,迟迟不愿离去归京。
《塞上曲》,娇甜的小颜凝曾坐在湖边凉亭里怀抱琵琶弹给他听,指尖诉尽衷肠。
那时候他还端着家翁的架子,抵死推拒她的心意,她爱而不得,弹得缠绵悱恻哀怨凄楚。
如今换做他来吹这支曲子,一样缠绵悱恻,一样哀怨凄楚,却多了太多悲恸苍凉。
她生死未知,他悔不当初。
旷野天边时有成群大雁飞过,只有雁,并没有凝。
他极目远眺,自嘲一朝失策,终究作茧自缚,落得茕茕孑立孤独终老。
可是孤雁难以独活,这鸟儿最为忠贞,为情生死相许,一修失偶,便不会再另配其他,只能在哀痛中了却余生。
生不如死,正如他一般。
如果,如果上苍垂怜,能给她一线生机,能让他找到她,此生绝不会再放开她分毫,不会再让她离开自己半寸,一定要日日夜夜拴在身边,如珠如宝娇宠一世。
这亘古不变的苍茫天地,可会予他点滴仁慈?
裘葛已更,星霜再换,然而走访了大大小小异族部落的谢阁老始终一无所获。
北狄本是大郑对各个外族部落的统称,不是每个部落都参与了大郑之战,各个部落之间关系也有好有坏。
尸体是肯定寻不到的,谢景修挨个儿打听寻人,因着他汉人身份,时常会遭到刁难敌意。
但只要他一亮大同总兵府的文书,对面便不敢再多说什么,毕竟狠狠吃了大败仗,锐气已被拔除殆尽。
尽管出门在外诸事不便,好在有厨神青黛在,花了整整两季,终于把脏腑受损的谢阁老调养得有了些起色,除开心境哀郁如旧,身体倒日渐康复起来。
只是细看之下,鬓角添上了几缕银丝,哀思深镂眉间,比起从前儒秀威严多了几分沧桑。
青黛看着这样的谢阁老,担心他会不会日日夜夜哀思难遣,最终落得中年华发,人未老头先白。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可她也和谢景修一样,哪怕希望再渺茫也好,她都不愿就此放弃,只能尽全力照料这位深情娇弱的首辅老爷,好让他再多坚持一段时间,万一人真的没死呢,万一真的找到了呢?
日居月诸,在外浪迹了半载有余的谢阁老一行游荡到一个傍林而居的叫察哈尔的小部落,一位高鼻深目自称名为塔娜的漂亮姑娘瞧见他们几人竟十分欣喜,问了来历之后便说要邀请他们在这里多留几日,然后欢天喜地地跑去通知别人了。
谢景修不明所以,下了马车舒展筋骨,等着看那姑娘去叫谁过来,远远望见一行四五匹快马撒腿飞奔而来,其中一人一身红衣,像天边一团赤色火云,脸上也围着红纱巾。
几人跑到谢景修面前勒马止步,背光面向他,他仰起头,在刺眼的阳光下微微眯眼,看清了马上之人。
这一瞬,在塞外异乡仿徨许久的谢景修胸口如遭重锤,目光定在那红衣少女脸上一动不动,呼吸滞涩,指尖微颤,耳中“嗡”地响了一下后什么也听不见了,只有心跳声仿若擂鼓。
整个世界似乎都静止了,连空气也凝结成块不再流动,只有那红纱在凭空飘舞,晃得他眼前一片绯色……恼人震颤,耳目晕眩。
那双圆圆亮亮的小鹿眼,那对似蹙非蹙的柳叶眉,是颜凝!是他那个朝思暮想的捣蛋儿媳妇!
他以为她死了,扎穿他的心脏,让它千疮百孔;碾碎他的魂魄,令它溃不成型;带走他半条命,独自逃离人间。
可她还活着,就在他眼前,手脚齐全,貌同初遇,恍若幻梦。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苦苦找了她那么久,每时每刻都在纠结于她的生死。
他以为她已成枯骨,以为她还活着是他一厢情愿逃避现实的借口,以为找她不过是他不愿面对她亡故事实的懦弱,然而她居然真的没死。
真的……还活着。
他的阿撵,终于被他找到。
“几位是从大郑来的?”那少女在马上居高临下俯视谢景修,开口朗声问他。
是颜凝了,这娇滴滴甜腻腻稚气未脱的声音,烧成灰谢景修也认得出。
可是为何她装作不认识,看到他双瞳之中也毫无波澜。
其他人见到她也震惊不已,又被她问得呆住,青黛急欲开口,谢景修却抬手制止了她。
他皱眉无声注视颜凝,把她看得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临大敌,心中忐忑不安,又一头雾水,正想要再问,他却忽而展颜温和一笑:“在马上俯视他人说话未免倨傲,你先下马,我再告诉你。”
颜凝承认这人说得有理,但感觉他方才的眼神有点吓人,心里瘆得慌,说话听上去和和气气的,可又有一种无形的威严,也不知为什么就老老实实下了马,走到他跟前抱了抱拳,再一次有礼有节地问道:“我也是汉人,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名字了,这儿的人都叫我苏布达。
敢问先生贵姓?可是从大郑过来?以前有没有见过我呀?”
“额……”
谢景修心念急转,颜凝眼神纯真坦荡,不似作伪,她说她不记得自己名字了,那就是前尘尽忘,失忆了?她虽然还活着,但却不记得他了。
“免贵姓谢,“谢行天罚”的谢,是从大郑来的。姑娘头纱遮面,在下不知你长相,如何答得出见没见过你呢?”
颜凝看这人似乎有些年纪,长相俊朗儒雅,鬓角略有几根银丝,梳得光洁整齐,说话文质彬彬,清瘦的脸上虽带着些塞外风尘,但站姿如松如柏,气度雍容不凡,心中已生了好感,解开头巾露出面目笑道:“我也不是要遮面,骑马时风沙吹得难受便用头巾挡挡。”
谢景修深吸一口气,目光沉沉凝视她,她没骗他,她没有死。
他的小阿撵还是原来那样,雪白的娃娃脸,挺翘精致的小鼻子,嘟嘟的花瓣唇,腮颊上是圆滚滚的嫩肉,一掐一个红印,笑起来两个梨涡,甜到人心底里。
一笑百花失颜色,一颦石木心碎。
她走后,一个相思细雨春,一个难耐蝉鸣夏,一个断肠孤月秋,一个哀寂茫雪冬。
又到一个绵绵草絮飞扬,子规夜啼血,白日小暖,和风微凉的初春,她回来了。
完璧归赵,合浦还珠。
谢景修压下心房颤动,对她莞尔说道:“对不住,我没见过你。那以后我就与这儿的人一起喊你苏布达姑娘可好?不知这名字在汉语里是何意呢?”
“行呀。”颜凝略微有些失望,看这人盯着自己目不转睛的样子,还笃定他认得她呢,原来并不是。
“苏布达是珍珠的意思,收留我的婆婆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查干苏布达,意为草原上的白珍珠。”
“原来如此。”谢景修颔首微笑,“你肤色白皙,想必起名字的人,是因此才称你为白珍珠。”
他面上笑得斯文,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要如何把这颗白珍珠挖了带走,“你既是汉人,为何逗留在关外,不回去找自己的亲人呢?”
颜凝叹了口气,面露难色。
“谢先生有所不知,我脑袋受了伤,以前的事都想不起来了,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自己亲人呢?
而且我身上也没有身份文牒,都不能堂堂正正地入关。
就想着我一直不归家,兴许家里人会来找我,所以才留在这儿,我若是到处乱走,家人反而更找不到我啦。”
“嗯,你说得倒也不无道理。”谢景修赞同道,心想幸好颜凝聪明。
她要是真的乱走,说不定他找个十年二十年也找不到她。
又问道:“那你家人要不来找你你准备怎么办呢?就一直留在这里吗?”
“嗯,这儿的人都很好,我也很喜欢大家,我就留在这里结婚生子好了。”颜凝笑吟吟地说。
谢景修瞳孔微缩,眯了眯眼,简直想立刻把她摁在腿上狠揍一顿。
他为了她伤到吐血数升卧床不起,又千里迢迢来关外天天吃风沙找她,日夜思念她,为她的逝去哀伤绞痛,可她居然乐呵呵地说什么要和别人结婚生子!
“真的吗?苏布达要留在咱们这,还要在族里选个丈夫?”
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听到颜凝这么说,欣喜地从马上翻身下来走到她身边,双目放光,激动地握住她的双手,“你选我吧!我喜欢你,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哪怕你想要天上的太阳,我也会想办法给你射下来!我阿木尔一定会让你成为草原上最幸福的姑娘!”
“额……”
青黛孟错书晴云素不约而同在心里暗叫糟糕,谢阁老哪里看得了这个,往日在家里颜凝和谢衡多说两句话他都要甩脸发脾气。
此刻被陌生男子求爱求亲,还被人握住了手,男女授受不亲,老头该不会要当场火山爆发吧。
“哈哈哈……”颜凝哈哈大笑,不以为意地抽回双手,“笑死我了,太阳是想办法就能射下来的吗?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啊。
还有说话就说话,不许抓我手,我可不爱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想让我选你也不是不行,只要你让我看上你,喜欢你,我自然就会选你了呀。”
“你让开,是我救了苏布达把她带回来的,汉人都说滴水之恩以身相许,她应该选我。”
另一个有些娃娃脸的瘦小伙也下了马围到颜凝身边殷切地看着她。
颜凝笑着摇摇头,果断拒绝。
“应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没说要以身相许呢。一码归一码,塞因你救了我,我是很感激你,也想报恩,不过这婚姻大事还得看两人有没有情意。
不然如果还有其他人也救过我的命,那我岂不是要嫁给很多人?毫无道理嘛。”
“呵呵,苏布达姑娘说得十分在理,婚姻大事,还得看是否两情相悦,切不可草率决定。”
谢阁老笑眯眯地看着接二连三被人求爱的颜凝,一肚子酸水都涌到喉咙口了,面上却不得不装得云淡风轻不露半点不悦。
马上还有一人冷眼旁观这一切,终于在此刻开口:“你们聊够了没有?再不走太阳都要落山了,你们要是不去我就一个人去。”
此人生得高眉深目,鼻梁笔挺,英俊非常,周身一股凛冽之气,说起话来也很嚣张。
谢景修清楚地感觉到,这人从一开始,眼睛就一直在他身上打转。
尤其是颜凝下马与他微笑交谈时,目光中的不快非常明显,而听到另两人向颜凝求婚,又一脸不屑一顾。
与小情人重逢的惊喜被这几个男人冲淡了大半,谢景修心里直冒火,他和颜凝不知道说了多少次要她矜持自爱,不要与男人调笑。
可她一出家门就拈花惹草,被一群觊觎她的男人争着抢。
还以为自己苦尽甘来,没想到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烦人!
颜凝回头看了看说话的人,随后对谢景修无奈一笑:“谢先生,我要和朋友们去打猎。您可务必在我们这里多盘桓几日,这里大伙儿最是好客,一定会尽心招待您的。我还有许多事想向您请教呢,回头见。”
她说完跨上马,身形轻盈潇洒,对谢景修一行人笑着挥挥手,视线在青黛脸上滞留了一瞬,随后遮上脸,和同伴们驭马转身离去。
谢阁老目送她离开,眉头打成死结,目光阴沉沉的像要吃人。
既然颜凝在这里,谢阁老便厚着脸皮向人家部落的族长请求收留他们几人,让他们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
他给了别人异常丰厚的回礼,都是他们草原上缺少的布匹器皿和药材。
因此族长很热情地给他们安排了三个帐篷,生活用具都准备周全,还说夜里大家要一起杀羊烤肉饮酒,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老爷为何不向阿撵说明真相,立刻带她走呢?”到了帐篷里,青黛一边帮谢阁老铺床整理衣物,一边忍不住倒出心中疑问。
“我当然想立刻带她走,可是她已经不认得我们了,你觉得该如何解释我的身份?我算是她什么人?”谢阁老淡淡道。
青黛的手顿时僵住。
是了,谢阁老和颜凝是公媳私通,这……要对她本人讲确实难以启齿,别说她未必信,就算信了也一定会心存抗拒。
可要是不说清楚,两人年纪相差那么多,怎么看也不是会郎情妾意私定终身的关系。
“先看看再说吧。我与她的事情现在朝中人人皆知,她既然不记得过去,那也未必一定要把她拉回去继续背负骂名。
她说喜欢这里的人,说不定已经另有新欢了,若是如此,难道我还能为了一己之私硬生生把他们拆散不成。
于我而言,只要她活着,过得好,已是感激上苍,别无所求了。”
谢景修说着,深深叹了口气,神情没落寂寥,把青黛看得心酸不已。
要是换做以前,她老早就去揪住颜凝的耳朵痛骂她了,怎么可以这样伤别人心呢!但这也不是她的错,谁也怪不了,都是命。
到了晚上,果然部落里几十号人都在草地上围坐成一圈,生了篝火烤肉饮酒。
花胡子族长老头到底见多识广,估摸着也看出谢景修气度不凡,怕是有点身份,对他态度殷勤,亲自挨个为他介绍了族人,原来白天那个傲气的英俊男子是族长之子,难怪这般不可一世。
谢阁老面带浅笑,对大家客客气气一一颔首作揖,比他在京师面对百官时不知亲切了多少,一点架子也没有。
颜凝已经与他认得,又都是汉人,族长便拜托她给谢阁老说说他们这儿的风土人情。
“可我得去宰羊呢。”小颜凝皱眉对族长说。
谢景修听得青筋一跳,几乎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他娇养在身边,除了看书吃饭偶尔被罚写字以外,一双素手什么都不用干的心肝宝贝,竟然要动刀子宰羊?
女儿家怎么可以干这种屠夫干的粗活!
还有她什么意思,宰羊比陪他说话更要紧吗?
郁闷的谢阁老强忍怒意对颜凝含笑温声说道:“无妨,我从没见过宰羊,陪你一起去吧,你不是说有很多事要问我嘛。”
半刻之后他便后悔了。
颜凝心软,先用内力掌击羊的额心,震碎它的脑仁让它死透了不觉疼痛才动手。
她手起刀落,一下割开那只羊的喉咙放血,随后拔出肠管打了个死结,接着纵向划开肚子,迅速剥掉一整张羊皮,再把鲜血淋淋的羊挂起来开膛剖肚挖出内脏……最后还割下了羊头。
太血腥了!谢阁老跑到一边狂呕不止,所以说君子远包厨,他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残忍恶心的场面,大理寺上刑都没那么可怕。
“谢先生您没事吧,喝口水缓缓。”颜凝很好心地过来帮他拍背顺气,还递水给他。
可是谢景修从她手上闻到了血腥味,又是一阵反胃,根本不想从她手里接水,拧着眉头瞟了她一眼。
“我觉得你手没洗干净,再去洗洗,上面还有血腥气,离我远点。”
“呃,那我把水放这了。”
颜凝担心地看看他,又去洗了一遍手才回来,“应该没味道了,您闻闻。”
她把那只谢景修再熟悉不过的小白手伸到他鼻子底下,令他心中一荡,血腥气什么突然就不重要了,他只想一口咬上去,在她软嫩的柔荑上印一圈牙印,然后挨个吮遍她细细的水葱指。
“谢谢你的水,刚才我吐得难受,说话不好听,对不住。”
到底没敢真的咬上去。
颜凝柔柔一笑,并不计较,她在火光下细看谢景修,见他已经换了一身衣裳,白天还穿着墨色凝氅,现在却是一件白缘蝶翅颜浣花锦直裰,腰间系石青绦,挂着一块黄玉玉佩,衣料上的曲水暗纹随着他的动作时隐时现。
这人真讲究,她想,才半天就要换一套衣服,爱打扮得很。
不过她不得不承认,这位谢先生身形颀长,面目俊雅儒秀,这沉稳大气的颜锦衬得他如美玉明月,既好看又不失温润含蓄。
谢景修却在烦恼别的事,颜凝在这个地方,身为女子却要宰杀牲口。
且不说杀生不祥,单论这活计的肮脏可怖,就不能让他的阿撵做,碰一下都不应该。
又嫌弃又心疼。
他叹了口气坐在一棵树桩上,文雅气派的举止与残糙的树桩格格不入。
“你想问我什么?”
眼前的人神色温柔,目光沉沉注视自己,颜凝突然忘了自己想问的事,小脸一红,有点尴尬。
“嗯……我想问什么来着?啊是了,谢先生从关内来时,有没有遇上或是听说哪户人家不见了女儿,亦或谁家名字里带“凝”或者“雁”的?”
谢景修心头一跳,不动声色看着颜凝问她:“你很想找回你的亲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名字里带了这两个字?”
颜凝略带忧伤地笑了笑,“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不是我有多想,只是万一有家人在担心我,而我行踪不明,或许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也不来找我,只顾着自己伤心,那就太可怜啦。”
说到这她从脖子里扯出一根红绳,下边坠了个透明小物,踟蹰了一下后取下绳子,把印章递给谢景修看。
“我身上有个琥珀印章,上面刻了“凝鸣雁舒”四个字,《凝鸣》诗经里有,宋祁则写过一首《舒雁》,但合在一起我就不明白了。
或许是我父母或是家人的名字,也可能是他们送给我的,刻了我的名字。”
谢景修接过印章,热乎乎的还带着颜凝的体温,他记得这个小东西应该是正好坠在她双乳之间的,胸腹忽而一阵躁动,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
这是他亲手刻的印章,她却说什么“父母送的”,实在令人心冷,谢景修看着印章上的字微微一笑。
“说实话,我不觉得这是父母会送的东西,你挂在颈间贴身携带,倒像是情郎送的。
说不定“凝”“雁”两字是从你们二人名中各取一字。
若真是如此,你的情郎还在痴痴等你回去,你却要在这里结婚生子,唉……可怜啊。”
“额……”
颜凝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个薄情的帽子,心里老大不舒服,但又觉得谢景修的话很有道理。
自己这年纪,有个喜欢的人也不奇怪,这东西万一是定情信物呢?
这人不送首饰珠宝,送个印章,想来也是个有雅趣的读书人。
谢景修看小颜凝盯着印章若有所思,又添油加醋地说:“你看,这琥珀里有一只红色的小蚂蚁,这叫红豆蚁,意表相思,十有八九是你的心上人给你的。
我看你还是不要和那几个男人纠缠不清了,不然哪天脑袋好了,突然想起了以前心爱的人,还不知怎么后悔呢。”
什么叫“脑袋好了”,我脑袋哪里不好了,受伤失忆而已,为什么要把人说得像犯病的笨蛋一样。
颜凝撇撇嘴看了谢景修一眼,从他掌心拿回印章戴上,不高兴地说:“我没有和人纠缠不清好吧。”
“没有那就最好了。”谢景修莞尔一笑,捣蛋鬼这气呼呼的脸蛋最可爱不过,让人想捏。
“如果让你在“凝”和“雁”两个字里挑一个做自己的名字,你想要哪个?”
“当然是“凝”啦。”颜凝毫不犹豫地嫣然回答,“凝多仙气,那可是神仙养在昆仑蓬莱的瑞禽。大雁土了吧唧的,因为不会叫被人射下烹煮了呢。”(典故出自庄周悲杀雁,本为不能鸣。)
“额……”
谢景修被她气得胸中气血翻涌,怒极反笑,眯起眼睛看着她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很有道理!”
颜凝莫名感觉背心升起凉意,头皮发麻,身上结起成片的鸡皮疙瘩,不敢再看谢景修,也不明白哪里得罪了他,只好移开视线讪讪地说:“羊肉要烤好了,谢先生去吃晚饭吧。”
一只羊已经烤得差不多了,白天那个要射太阳的小伙子给颜凝切了一盘子羊腿肉端给她,油光闪闪香气四溢。
“谢谢。”颜凝接过盘子对阿木尔甜甜一笑,阿木尔红着脸喜滋滋地走了,谢景修看得火大,脸色就不怎么好。
“谢先生也尝尝吧,是为了您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才烤的羊呢。”
颜凝把盘子递给谢景修,他想起刚才血淋淋的场面毫无胃口,皱眉推拒道:“我不爱吃羊肉,而且没有筷子没法吃。”
其实颜凝也谈不上爱吃羊肉,但现杀现烤的确实吃起来香,这位矫情的客人连尝一口都不肯,未免太可惜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饿肚子吧。筷子我们有,您先坐着,我去给您拿一双过来。”
小颜凝温软大度,对上谢阁老这么难伺候又不给面子的人也不生气,她刚起身想走,就被谢景修隔着衣袖握住手腕。
“我的随从会拿给我的,倒是你,没筷子你准备用手抓吗?”
“大家都用手抓啊,啃羊腿怎么用筷子呀。”颜凝低头看了看被抓住的手腕重新坐回谢景修身旁,对他的疑问不以为然。
“你在关外待得久了,连饮食礼仪都不要了。”谢景修很是不悦,轻轻叹了口气。
这话听着古怪,好像他很熟悉自己一样,颜凝心中又生出白天初见他们一行人时的异样感,他真的不认识自己吗?
云素果然拿了碗筷过来给自家老爷,颜凝一看,汝窑青瓷葵花碗,包银雕花红木筷,恁讲究。
谢老爷大大咧咧把碗伸到颜凝面前,“看在你辛苦一场的份上,我就尝一口试试。”
颜凝听他改了主意十分高兴,可刚才他还在嫌弃她不讲礼仪,现在当然不好拿手抓肉给他,她想了想便要去拿谢景修手里的红木筷。
“麻烦谢先生筷子接我一用。”
谢景修把筷子给她时故意碰到了她的指尖,颜凝一惊,抬眼看了看谢景修,见他也在看自己,目光一对上就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去微微红了脸。
要的就是她脸红害臊,某人目的达到,展颜微笑,“你怎么不夹给我?”
颜凝吸了口气抬起头来,从自己碟子里夹了一块肥瘦相间的羊腿肉放到青瓷碗里,把筷子递回给谢景修,有点期待地望着他。
没办法,为了让小美人高兴,谢阁老强忍恶心,夹起羊肉,咬了小小一口。
因为加了胡椒孜然,肉又新鲜,香辣之下并无多少膻腥味,意外地还算可以入口。
不过偏爱江南精致小菜的谢大人对这种粗豪的大块烤肉,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
“还算不错,只是我确实不好食肉,尝一块便够了,剩下的你自己吃吧。”
“可是一块肉怎么吃得饱呢?”颜凝愁眉苦脸地看着他,心想让客人饿肚子可不行,会丢族长的脸。
“那我去给谢先生下碗面好不好?汉人应该都能吃面的。”
什么叫汉人能吃面,难道你不是汉人吗?不过还真没吃过颜凝亲手下的面,谢景修想也不想就应下说好,一点不客气。
“那您等我一下,很快的。”颜凝笑笑把羊肉放下走了。
这一次谢景修没有说要陪她去,之前宰羊的刺激太大,他已经不太敢尝试陪她做他不熟悉的事情了。
谢阁老扫视围着篝火饮酒吃肉的众人,北狄习俗与大郑大不相同,没有那么多罗里吧嗦的礼教束缚,男男女女同席而食,言谈欢笑毫无避忌,加之草原牧民天性奔放,三杯酒下肚便开始载歌载舞。
怪不得阿撵喜欢这儿,他心道。
不多时颜凝就端着一碗热乎乎的面条过来了,这一次讲究的谢阁老没有再挑剔,就着她拿来的土瓷碗斯斯文文撩起几根面条尝了一口……
难吃至极!还不如吃羊肉呢。
“这什么面?”谢景修忍住讥讽她的冲动,好声好气问她。
“青稞面呀,我们这里麦子的白面少,大多是粗粮面。”颜凝微笑着甜甜回答。
青稞面谢阁老这半年来也吃过不少了,这么难吃的还是头一次遇到。
可是这是小阿撵特地为他亲手做的,她一双亮晶晶地大眼睛还这样期待地看着他,像一只等主人褒奖的小狗,只缺一条尾巴给她左摇右晃了,该怎么办呢?
可怜的谢景修只能硬着头皮吃了小半碗,最后实在咽不下去,推脱已经吃饱,终于憋不住对她说:“我身边有个丫鬟叫青黛,就是那个长得高高瘦瘦眉目清秀的姑娘,她厨艺绝佳,今天看到你又觉得十分投缘,你若得闲不如去找她聊聊,跟她学点手艺。要是做得像她一样好吃,我兴许还能再多吃几口。”
意思是说我做得难吃吗?颜凝嘟了嘟嘴,心道这老头看着斯文客气,又矫情又挑剔,说话还不中听,哼,谁要做给你吃。
“你不服气就自己尝尝。”谢景修又补上一刀。
“好!”颜凝还真的不服气。
于是心机的谢阁老一手拿碗,一手挑了一筷子面凑到颜凝嘴边,竟然作势要亲手喂她。
“啊……谢先生,我还是自己来吧。”颜凝不知所措地涨红了脸。
“不要啰嗦,张嘴!你不自己吃一口,还以为我在冤枉你。”
谢景修板着脸,口气严景语音低沉,透出一种不容拒绝的威势,颜凝被他一瞪,不情不愿地张开小嘴,怯怯地看着他,又羞又为难。
他的眼神太古怪,初看温和,再看霸道,看久了,里面影影绰绰都是郁郁深情。
塞外难得遇见汉人,小颜凝莫名地想亲近他,又怕他,对他好奇,又不敢深究。
他的眼睛里究竟藏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看她?
面条喂到她嘴里,他吃过的筷子碰到了她的舌尖,殷红的花唇努力把面嗦进去,一动一动地勾引着谢景修。
他盯着那对樱唇看着看着,就想起她亲吻他性器捉弄他的样子,就是这对唇,对他做过那种淫冶的事情……
“嗯……对不住,好像是不怎么样。”
颜凝艰难咽下面条,抱歉地看着谢景修,不是人家挑剔,是她自己废物,还劝着这个矫情的人吃了那么多,就怪不好意思的。
“罢了,面好不好吃都无所谓,你这一番心意已经让我如获至宝了。”
谢景修莞尔一笑,俊美无俦,取出他的丝帕随手替颜凝抹去了下唇上沾的汤汁。
颜凝猝不及防,愣怔在那里,心脏漏跳一拍。
最后那个笑容和那句话让颜凝心脏“砰砰”直跳,她感觉这位谢先生对自己的企图太明显了,才认识多久就又喂吃的又帮擦嘴。
虽然并非是什么摸手摸脸的狎亵轻浮之事,但若论亲昵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他偏偏一脸正色,行止文雅,言语也居高临下地没半点轻侮调笑,还时不时来两句惹人生气的话,令她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
到底什么意思?
这里两人各怀心思地沉默着,气氛变得暧昧粘稠,烤肉混着香料的刺鼻气味到他们这里却变得酸酸甜甜。
然而有的人却实在看不下去了,白天那位英俊高傲的青年大步走来,在他俩面前站定,低头冷冷盯着谢景修,嘴里对颜凝说道:“苏布达,你是自己没手吗?吃东西要别人喂?”
颜凝一听就知道他吃醋了,也懒得辩解,趁势起身对这人淡淡说道:“奥尔格勒,我做的面太难吃了,客人吃不惯。你帮我跟族长说一声,我送他回帐篷休息了。”
“为什么他回帐篷要你送?他不认得路吗?”
奥尔格勒听到颜凝这么照顾这个装模作样的汉人,心里更是恼怒,面色冰寒质问她。
谢景修低头微微一笑也站起身来,并不与这人说话,只是对着颜凝温声说:“没关系,你不用操心我,不至于就走丢了,别为了我和朋友伤了和气。”
他这样说倒让颜凝又多生出几分歉疚,又看他神色似乎有些落寞,胸中就有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可是狂傲的奥尔格勒不好打发,她只得点点头。
“那您好好休息,明天我去找青黛姑娘让她帮忙看看我这双手还有没有救。”
谢景修闻言失笑,凝目看了她一会儿,恋恋不舍地柔声说:“你也好好休息。”
说完对奥尔格勒随意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背负双手转身离去。
在别处候着主人的云素和书晴立刻过来收了自家碗筷,对颜凝意味不明地嫣然一笑,跟随主人一起走了。
孟错一直在旁留意这边保护主人,见状也带着青黛走了。
颜凝心想这位谢先生带的侍从仆人都会鉴貌辨色,而且忠心得很,这人家里想必不一般,不知为什么会来关外。
“你怎么还做面给他?”
谢景修一走,奥尔格勒就放下刚才充满敌意的姿态,面色语气也缓和下来,走近颜凝皱眉问她。
“他吃不惯我们这儿的东西,你老爹让我多看顾着,我也是好心,可惜实在是没下厨的天赋。你别老对别人凶巴巴的,小心被你老爹骂。”
“我明天就叫老头子让他滚蛋,我看他对你不怀好意,你别傻乎乎的被人调戏了还不知道。”
奥尔格勒喜欢颜凝,他早就私下告诉过她,尽管颜凝没答应。
但以他的英俊,族里喜欢他的姑娘那么多,他相信颜凝早晚也会被他俘虏。
现在被一个外来人横插一脚,原本笃定的心焦躁起来,那人看上去十分奸猾,他得快点下手把颜凝抢过来。
颜凝心大,只觉得这位谢先生长得好看却行径古怪,她照常吃得好睡得香。
可谢景修却不像她这么想得开,当夜就梦见白天见到的三个男人围着他的阿撵,一个个轮流亲她抱她,到后来竟然一起动手,三人紧紧环住颜凝,一左一右舔她耳朵,还有一个吻她口唇。
可怜的小颜凝手足被缚不得反抗,泪流满面地用眼神向他求救,他气得肝胆俱裂,惊怒之下拔剑冲过去想要砍人,奋力一挥却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冷汗。
一定要带她走,不管她是不是另有新欢,就算真的有了,他也要拆散他们!
次日,行动迅速的孟错在到处查探了一圈后,为忧心忡忡的首辅大人带来了他想要的答案。
“大人,属下查清了,颜姑娘是被收尸人从尸堆中捡回来的。
她头上中箭,但尚有呼吸,又是女子,那个叫塞因的少年搬尸人就偷偷将她背回这里掩藏起来,交给此处巫医老妪萨仁。
因她醒来后记忆全失,无处可去,便留在此地养伤至痊愈,做了这个部落的大夫,给那位巫医当助手。”
“嗯。”这些和谢景修猜测的大致不差,“那三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位叫塞因的少年,是巫医萨仁的孙子,从救了颜姑娘之后就对她生了情意,此人性情软弱温善,颜姑娘只当他是恩人友人。
另一位叫阿木尔的也对颜姑娘情有独钟,他是此处的摔跤高手,性子爽朗外向古道热肠,对孤身一人的颜姑娘诸多照顾,只是颜姑娘对他似乎也只是朋友之交。
还有一位奥尔格勒是族长的次子,性子高傲,自视甚高,他对颜姑娘最为执着,颇有一股势在必得之意,另外两个情敌都不放在眼里。”
“哦?那颜凝呢?”谢景修手指轻扣桌面,忍着不快耐心听了半天,发现孟错说到这里语气有些异常,抬眸看向他问道。
孟错有点想笑,稳住声音恭敬答道:“她似乎……似乎对此人十分厌烦,非但当众拒绝过他的求爱,平日里也常常躲着他绕道而行,一点面子也不给这人。”
谢阁老终于知道他笑什么了,在大漠寻找颜凝踪迹的这半年,青黛对他们说了不少她在荣亲王府时的事迹。
对于她看不上眼的人,颜凝可说是无情至极,别人送的东西不是被她一口回绝,就是视若草芥弄得面目全非。
要是人家缠她缠得紧了,她就直接找荣亲王告状派侍卫把人赶得远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朵高岭之花,难以攀折,谁能想到她进了谢府在公爹面前竟然会是这么一副娇羞黏腻的模样。
这下谢景修终于放下了大半的心,情敌多是多了点,可一个个都不禁打,阿撵早晚还是他的。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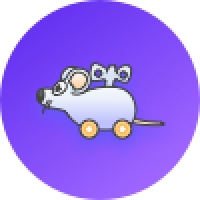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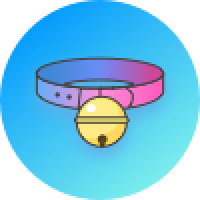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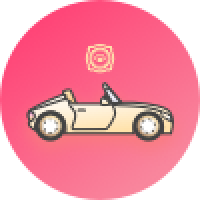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