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太极殿。
“吾皇万岁!”群臣俯身齐呼。
“平身吧!”北靖皇帝萧云蜃抬手道,他今年四十岁,正值壮年,俊颜雅貌不说,气度尤为雄迈。
萧云蜃的祖父便是北靖太祖皇帝萧恭,当年大周内乱,他乘势兴起义兵,讨伐无道昏君,短短十年便据有半壁天下。
正当他志得意满,准备饮马长江,统一天下之时,却猝然驾崩,临终时托付大将军宗政伏远辅佐太子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太宗皇帝。
当时太宗皇帝年弱,不过十一二岁,主弱臣强,朝野上下尽是观望之人,但宗政伏远却无丝毫逾越之举,上下恭谨,待太宗皇帝成年后,又立即归还大权,遂赢得天下美名。
太宗皇帝感念其诚,不仅使其位比亲王,还将自己的胞妹嫁给了他的独子宗政长玄。
只可惜太宗皇帝躬勤政事,以致英年早逝,临终时仿效旧事,命其独子宗政长玄辅佐太子萧云蜃登基。
“谢陛下!”群臣谢过之后,方才各分文武,站至一旁。
“陛下有旨,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一名内侍尖声唱道。
“启禀陛下,微臣有事启奏!”监察御史张寥站出来道。
“说!”萧云蜃挥手道。
张寥道,“前番时日陛下命臣彻查清河镇被屠戮之事,微臣现已查明,现具表上奏。”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本文书,双手奉上。
站在后方的宗政元恒一听,顿时心中一紧,清河镇之事他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
一名内侍急忙过来将文书送至萧云蜃面前。
萧云蜃拿起文书,说道“你继续说!”说罢,他便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现已查明,屠戮清河镇的凶手,乃是北戎十三部中的莫度部,其等乘着寒阳军镇松懈之时,偷渡入关,见清河镇繁华富庶,便在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致我数千大靖子民惨遭毒手!”张寥大声说着,言语之中尽是悲痛之情。
“啪!”萧云蜃将文书砸在御案上,怒声道,“寒阳军镇是谁把守,怎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张寥躬身道,“乃是豹韬卫大将军谢权,当时巡视的军士发现莫度部南下,急忙禀报请其定夺,但寻遍军营也不见其人!”
萧云蜃闻言大怒,“他去哪儿了?”
张寥欲言又止,偷偷看向站在右侧首位的丞相谢渭,不知该如何言说!
“说啊!”萧云蜃大声怒道。
张寥硬着头皮道,“后来发现他在女营之中!”
话语刚落,朝堂上顿时一片讥笑之声,所谓女营其实就是妓营,因为边塞苦寒,为了抚恤将士,朝廷特意设置了女营,编入罪臣妻女及风尘女子。
按理来说,将士们去女营寻欢作乐倒也正常,但一军主将跑去女营厮混,还被敌军寻到时机那问题就大了,说明这家伙在女营的时间比在军营的时间还要多。
果然,饶是皇帝萧云蜃宠爱谢权,现在也是气得发抖,心道此人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启禀陛下,老臣有事启奏!”谢渭站出来道,他已年过七旬,历经三朝,与宗政伏远同辈。
“说吧!”皇帝萧云蜃抑制怒气道,谢渭的脸面他还是要给的,毕竟他最宠爱的谢贵妃就是谢渭的女儿,谢渭算得上是他的岳父。
谢渭再是躬身一礼道,“豹韬卫大将军谢权玩忽职守,以致酿成大祸,老臣请旨从重处罚,以儆效尤!”
旁下群臣大为惊讶,面面相觑,难不成这老狐狸准备大义灭亲。
梁王宗政长玄与太子萧彻相视一眼,却是从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出一丝凝重之色。
果然,皇帝萧云蜃闻听此言,心头的怒火顿时去了九分。
谢权有多少本事他是知道的,当初要不是他坚持,谢权也当不上豹韬卫大将军之职,如果轻易拿下,恐怕会损害他的威信,但谢权前后数次惹出大祸,却是不能再担任此职了。
就在皇帝纠结之时,梁王宗政长玄站出来道,“启禀陛下,臣有事启奏!”
“梁王直说无妨!”皇帝萧云蜃有些心烦意乱道,他知道梁王宗政长玄向来与丞相谢渭不睦,现在站出来,不外乎落井下石。
可谁知,宗政长玄却丝毫不提谢权之事,反而说起另外一件事,“启禀陛下,月前陛下命我整顿京畿守军,臣现已整顿完毕。京畿守军共编六军八万余人,只是还缺少一名统军大将,臣不敢逾权,特请陛下定夺!”
皇帝萧云蜃听着奏报顿时眼前一亮,什么缺少统军大将不敢越权,这分明是搭梯子给自己下嘛!
皇帝萧云蜃轻轻咳嗽一声,嘉许道,“梁王忠贞体国,当为天下表率!”
他看向一旁的内侍,“传旨,赐梁王黄金三千两,玉石百件!”
“诺!”内侍应声道。
皇帝萧云蜃回过头来道,“豹韬卫大将军谢权遗怠战机,不可为边军大将,即日起改任京畿守备值守!”
“诺!”群臣俯首应道,心里却是滋味不一,要知道京畿守备值守与豹韬卫大将军俱是正三品之职,看来皇帝对谢氏一族的宠爱还在他们推测之上,哪怕谢权犯下如此大错,却只是改任而已。
此时,站在右侧首位的谢渭却对着宗政长玄微微抬手,权做感谢之状。
宗政长玄也是微微颔首示意,站在他一旁的平西侯柳疾见此心中大为不解,原本想趁此机会将谢权拉下马,折断谢氏的一条臂膀,可在最后关头梁王宗政长玄却不知何故放了他一马,这使他颇为不甘。
宗政长玄连忙使了一个颜色,将他安抚下来。
了却了一桩麻烦事,皇帝萧云蜃颇为高兴,问道,“各位爱卿,可还有要事禀奏?”
这时,宗政长玄又站了出来。
“启禀陛下,前些时日老臣寻回遗失在外的亲子,现恳请陛下下旨,录其姓名于宗谱之上,以正世子之位,将来也好继承梁王爵位。”
言语刚停,朝堂内顿时一片私议之声,梁王宗政长玄寻回亲子之事在长安城已然传闻许久,只是一直不见梁王府动作,今日宗政长玄于朝堂之上公开请旨,看来已经做好了将儿子推出来的准备。
皇帝萧云蜃沉吟道,“既然如此,那便命其上前,让我好生看一看。”
内侍立即扬声道,“命宗政元恒上前觐见!”
宗政元恒当即从末尾站出来,疾步走到御前,跪拜道,“微臣宗政元恒拜见皇帝陛下!”
“放肆!”宗政元恒才刚刚说完话,御史大夫周进立即站出来驳斥道,“你并无官职在身,怎么可以自称微臣,应当自称草民才是。”
宗政元恒却丝毫不做理会,双目犹自直视前方,不发一言,使得御史大夫周进颇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这时,站在武将一列的平西侯柳疾站出来反驳道,“周御史有所不知,前些时日梁王殿下已经任命宗政元恒担任骁骑校尉一职,职衔五品,已在兵部备案,想来是周御史闭门读书,不曾听闻罢了!”
“你!”被平西侯柳疾反呛了一句,御史大夫周进顿时气得七窍生烟。
“好了!”皇帝萧云蜃出来打了一个圆场,“不知者不怪嘛!”
他对着宗政元恒道,“且抬起头来,让我看一看!”
宗政元恒于是缓缓抬头,露出坚毅而俊逸的面容。
皇帝萧云蜃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不住地点头,若是只从相貌上来看,宗政元恒是宗政长玄的亲子当是毫无疑问,二人非但相貌酷似,眉眼间的那股英气也是一脉相承。
旁下群臣也是点头不止,这副相貌错不了!
就在皇帝萧云蜃准备开口说话时,一旁的秦王皇甫瞑站了出来,“启禀陛下,臣有事启奏!”
宗政元恒用眼角余光望去,只见其人年约五旬,一副鹰目狼视之相,使人望而生畏。
“爱卿请说!”皇帝萧云蜃笑道。
“谢陛下!”秦王皇甫瞑接着道,“臣听闻梁王世子今年只有十七岁,如此年纪便担任五品骁骑校尉,恐会落人口实,臣建议陛下选派宫中宿将与其比试,以正试听,也让我们这班老臣好好见识梁王世子的武艺!”
“哦?”皇帝萧云蜃略微沉吟了一下,秦王皇甫瞑与梁王宗政长玄向来不睦他也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秦王皇甫瞑竟然会在梁王继承人问题上站出来挑战宗政长玄,看来二人的关系又恶化了许多。
但这一切又是他喜闻乐见的,梁王宗政长玄权柄过大,有威震主上之嫌,实在是令他寝食难安,有秦王皇甫瞑制衡一二,倒是让他轻松许多。
只是刚才梁王宗政长玄提前释放善意为他解围,现在自己如果不投桃报李,恐怕以后君臣之间就难有如此默契了。
就在皇帝萧云蜃难以决断之时,丞相谢渭站出来道,“启禀陛下,老臣有事启奏。”
皇帝萧云蜃挥手道,“但说无妨!”
谢渭捋须道,“老臣以为,宗政元恒乃是梁王亲子无疑,可先下旨承认他的梁王世子之位,再令其比武以正视听!”
“好,丞相所言有理!”皇帝萧云蜃大喜,如此以来,便可既不得罪梁王宗政长玄,又能令两家相争,实在是一箭双雕!
此时站在一旁的秦王皇甫瞑当即恶狠狠地看了丞相谢渭一眼,他方才建言,让宗政元恒与宫中宿将比试,便是想让宗政元恒不能顺利继承梁王世子之位,可谁知谢渭这一说直接让他的打算落空,怎能让他不恼!
皇帝萧云蜃转首吩咐内侍道,“命凤阁拟旨,即日起宗政元恒继承梁王世子之位!”
“诺!”内侍领命而去。
皇帝萧云蜃回头看向秦王皇甫瞑询问道,“秦王既然建言比武,不知可有人选?”
秦王皇甫瞑道,“殿前值守皇甫敬武艺高强,为人谨慎,当是不二人选!”
平西侯柳疾闻言微怒,站出来反对道,“不可,皇甫敬年过四旬,更有六级巅峰修为,而梁王世子不过十七岁,初涉武道,如此比试,岂不是以大欺小!”
秦王皇甫瞑对着平西侯柳疾自得满满地摆手道,“老夫也是武道中人,武道一途不分老幼只论高低的道理我还是懂得。”
接着他阴恻恻道,“前些时日,平南侯府举行清平宴,梁王世子于宴会上大展拳脚,可是威风得紧,怎么今日就不行了呢?”
原本目光低垂的梁王宗政长玄此时目放精光,微微侧首,深深看了秦王皇甫瞑一眼,此人几次三番作祟,打乱他的布置,已然激怒于他,待此事了结,他必然要对皇甫一族狠狠敲打一番。
被梁王宗政长玄扫过一眼的秦王皇甫瞑此时一阵发寒,好像被饿狼盯上一般,见平西侯柳疾不再说话,便退回原位。
“咚咚!”皇帝萧云蜃敲了敲桌子,结束了几人无谓的争吵,他对着梁王宗政长玄问道,“不知梁王以为秦王的建言如何?”
梁王宗政长玄拱手道,“老臣以为秦王的建言完全可行!”
“哦?”皇帝萧云蜃又回头望向宗政元恒问道,“你是否愿意与皇甫敬比武?”
宗政元恒跪拜道,“微臣一切谨遵陛下钧令,绝无二话!”
皇帝萧云蜃心头一喜,对宗政元恒的回答非常满意,虽然他不喜欢梁王宗政长玄,但对他这个儿子却很有好感。
“好,摆驾校场!”皇帝萧云蜃起身道,身旁的内侍急忙前去准备銮驾。
“诺!”群臣俯首后,这才鱼贯而出,向校场而去。
趁着这个空隙,梁王宗政长玄并排走到丞相谢渭身旁,“方才多谢谢相相助!”他难得面色柔和道。
丞相谢渭微微摆手,笑呵呵道,“该说一声谢字的是我才对,刚才若非是梁王相助,恐怕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早被陛下军法从事了!”
说到这里,他唏嘘道,“你我二人平日里虽有争执,但说起来你我为了国事,论及以往你我两家却大有渊源啊!”
“哦?不知谢相所谓渊源是何事?”梁王宗政长玄不解道。
谢渭解释道,“当年我与伏远公初识时,曾有戏言,生子则为异性兄弟,一男一女则为夫妻,只是后来太宗皇帝下嫁太原公主于你,这才按下此事不表,老夫思及于此常引以为憾事!”
梁王宗政长玄闻言叹道,“看来谢相与我宗政氏确实渊源不浅!”话是这样说,但宗政长玄心中却不以为然,这老鬼说话不着边际,反正伏远公已逝,无人作证,只得任由他说。
丞相谢渭此时目光一转道,“老夫听说梁王正在为世子挑选良配?”
梁王宗政长玄回道,“不错,我宗政氏一脉单传,人丁不旺,元恒既已成年,正好开枝散叶,光大族门!”
丞相谢渭点点头道,“此事确实刻不容缓,不知梁王看中了哪一家的姑娘?”
梁王宗政长玄摇头道,“只是刚有此意,尚无头绪!”
“正好!”丞相谢渭拍手叫好道,“老夫这里却有一良配,不知梁王是否称意?”
“哦?”梁王宗政长玄浓眉一紧,不知谢渭说这话打得是什么主意,竟然比他还上心,“不知是哪位贵人?”他问道。
丞相谢渭道,“谢贵妃得陛下宠幸,生诞一男一女,男即城阳王萧翰,女即金阳公主萧淑,诸多公主中以其最得陛下宠爱,正好与世子相配!”
谢贵妃便是谢渭的小女儿谢黛玉,天生丽质不说,更是少有的绝色美人,当年皇后去世,谢渭便着手安排女儿入宫,一举俘获帝心,十六年来宠幸不减,谢渭能稳立朝堂便有这层缘故。
宗政长玄为难道,“可是据我所知,金阳公主今年才十二岁,与元恒相差甚远!”
谢渭摆手道,“不过相差四五岁,何来相差甚远,梁王又何必推辞,难道是看不上这桩婚事?”
“岂敢!”宗政长玄急忙道,“如果此事能成,当是我宗政氏之幸!”
谢渭一把抓住他的臂膀道,“好,既然梁王话都这样说了,那老夫自当竭尽全力,玉成此事!”
说完,二人好似多年好友一般,哈哈大笑,并行而去。
皇城校场。
皇甫敬正整束铠甲,活动身体,他躯干魁梧非常,面如熊虎,乃是一员沙场悍将,曾在北军任职,杀得北戎人哭爹喊娘,前些年才调回长安,过了几年舒服日子。
方才比武的消息传来,他内心毫无波澜,对手不过是一名乳臭未干的少年,实在是让他这种沙场悍将提不起半点兴趣。
此时身后的脚步声传来,皇甫敬转头一看,立马单膝跪下,“侄儿见过家主!”
来人正是皇甫瞑!
皇甫瞑摆摆手道,“起来吧!”
待皇甫敬起身后,他看向皇甫敬道,“待会儿你出手重一些,想来宗政长玄也无话可说!”
皇甫敬抱拳道,“诺,侄儿一定会狠狠教训这小子一顿!”
皇甫瞑见他丝毫没把宗政长玄放在心上,不由得提醒道,“你小心些,千万不要阴沟里翻船,伍教头认为这小子的武道修为绝不在五级之下,也不知这小子是怎么修炼的,才十七岁就有如此修为,与他比起来,玉龙却是远远不如!”
“哦~”皇甫敬闻言微讶,才十七岁便有五级修为,说是妖孽也不为过,江湖中大多数人突破五级修为都在三十岁左右,便是皇甫一族倾心培养的皇甫玉龙也是二十四岁才有四级大成修为。
想到这里,皇甫敬收敛方才的轻视,变得郑重起来,“家主放心,他便是再厉害也不过五级修为,自我突破六级以来,还没有一个五级武者能从我手里轻易走脱的!”
“嗯!”皇甫瞑微微点头,心中安定不少。
与此同时,校场另一边,宗政元恒已更换武服完毕,平西侯柳疾正耐心地为他介绍即将交手的对手。
“皇甫敬乃是六级顶峰修为,虽然距七级修为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六级武者中却是佼佼者的存在,他一身横练功夫,体坚如钢,再加上赖以成名的开碑手,凶猛异常,世子绝不可与其正面交手,应以游走为上策,只要能撑过三十招,便是不胜也胜了。”
“嗯!”宗政元恒明白柳疾的意思,但这是他第一次出手,绝不可示弱,否则后面麻烦会更多。
通过今日的朝会,他隐隐有所感悟,朝堂上的对手是绝不会因为你示弱而手下留情的,只有当你无法威胁到他们时,他们才会停止出手,与其示弱讨好他们,还不如表现够的尊重讨好皇帝。
此时校场边上,皇帝萧云蜃已经入座,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上的二人,各大臣也已入座。
一名身着华服面相阴柔的青年迈步来到宗政长玄身旁,一名大臣冷不防回头看见其人,讶然一惊,急忙起身作礼,让开席位。
青年微微一笑,入座后言道,“那皇甫敬可是六级顶峰修为,梁王难道不担心吗?”
此人便是太子萧彻,今年不过二十四岁,乃是先皇后嫡出,与宗政元恒在平南侯府所见的清河公主一母同胞,只是自从谢贵妃得宠后,皇帝萧云蜃屡次动念废除他太子之位,改立城阳王萧翰为太子,所幸一帮老臣屡次谏阻,这才未能实施。
宗政长玄神色泰然,“身为人父,自然是担心,可我宗政氏男儿向来不惧刀山火海,更何况是一场比武。”
太子萧彻点点头,没在说什么。
比武场上,宗政元恒与皇甫敬抱拳作礼,便各自后退一步,摆开架势。
“铛”的一声钟响,比试开始!
皇甫敬身形一动,宗政元恒刚反应过来,他便已欺身上前,右手如刀劈下。
宗政元恒当即一个侧身,手刀堪堪顺着他的鼻梁而下,带动的劲风甚至让宗政元恒的面庞生疼。
一击不中,皇甫敬立即变招,如庖丁解牛,斜劈而去,直击对方腰腹。
宗政元恒岂能让皇甫敬如愿,右手金光大放,迅雷一击斩在皇甫敬手腕之上,正是他所炼的炼金手!
嘭!皇甫敬身形不稳,当即连退六步这才稳住身形,手腕上一阵酥麻,几乎无法握拳。
对面的宗政元恒也是连退六步,才止住身形,他微微失望,刚才自己可是动用了全力,竟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好厉害的炼金手!”皇甫敬心道,方才他虽是试探,但也用三分内力,想不到竟被对方一击而退。
他站直身子,微微舒展腰背道,“小子,接下来我可不留手了!”话音刚落,他周身劲气激涌,六级顶峰的武学修为展现地淋漓尽致。
“在下乐意奉陪!”宗政元恒高声道。
“哼,让你见识一下六级高手的厉害!”皇甫敬轻哼道,身形猛扑而至,开碑手大开大合。
宗政元恒当即以移形换影身法和炼金手应对,能避就避,不能避就全力应对,仗着一身神力,三十回合下来也未落下风。
校场外,皇甫瞑越看越气,本是想打压这小子的势头,可看现在的模样,反倒是让这小子出尽了风头。
校场外,一帮略懂武道的老臣看得津津有味。
宗政元恒的躲闪在他们看来一点问题也没有,皇甫敬势大,唯有暂避其峰,徐徐图之,如果宗政元恒傻愣愣地上去和皇甫敬硬碰硬,那才是让他们失望。
便是皇帝萧云蜃看了也不住点头,宗政长玄这个儿子无论武艺还是心性都是上上之选。
“嘭!”皇甫敬一击不中,面前被他的手刀破开一个大坑,尘土四散。
他羞怒道,“小子,如果你再逃下去,恐怕这场比试永远也结束不了!”
宗政元恒在他不远处立定下来,笑道,“我接下来不会再逃了,咱们一招定胜负如何?”
“狂妄!”皇甫敬气急而笑,以他的修为便是七级高手也不敢说能一招胜过他。
宗政元恒没再多说,通过刚才的交手,他已经试探出皇甫敬的真实修为,并且打乱了皇甫敬的进攻节奏。
他双目一闭,双手缓缓抬起,至阳神功飞快远转,藏在他胸口的猛虎猛然活了过来,张牙舞爪,似乎想要破开他的胸腹跳将出来。
这是宗政元恒的家传秘法,他的气势在急速拔升!
站在他对面的皇甫敬像是看见怪物一般,无比震惊,江湖上也有这类刺激人体潜能提升内力的秘法,可这些秘法一来非常残忍,二来提升有限。
可当宗政元恒的气势稳定下来后,皇甫敬感知到宗政元恒内力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如果说皇甫敬的内力修为是六级顶峰的话,那宗政元恒的内力修为已经达到了准七级的地步。
“皇甫将军,小心了!”宗政元恒轻笑道,他身形一动,一掌猛然拍出,“空寂掌”!
“装神弄鬼!”皇甫敬不屑道,他倒要看看宗政元恒是不是真有准七级的内力,当即鼓动全部的内力,对着宗政元恒的掌印拍了过去,“开碑掌!”
“不要!”在校场外的秦王皇甫瞑霍然起身制止道,身为秦王,他的武学修为足以列入一流高手之列,达到了七级中阶的地步,虽然难以相信,但宗政元恒的内力拔升在他感知中却是非常真实的。
以二人现在的修为差距,皇甫敬是绝对敌不过宗政元恒的。
果然,二人才一碰撞,皇甫瞑便惊悚地望见皇甫敬狂吐一口鲜血然而倒飞而出,而宗政元恒却仍旧屹立不倒!
校场旁的武官们见此,立马蜂拥而上,扶起皇甫敬,检查伤势。
“禀报陛下!”一名武官高声道,“殿前值守皇甫敬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宫门口,大臣们渐渐散去。
丞相谢渭掀开轿帘对随从道,“你去盯着梁王府的人,看他们出宫后去了哪儿,回来报我!”
“是!”随从低眉应声道。
回到府中,谢渭才在侍女的服侍下脱下朝服,换上一般衣物,次子谢骏便急匆匆赶来,埋怨道,“父亲,刚才在朝堂上你怎么帮梁王说话,方才我回来时遇见秦王,他对孩儿的脸色很是难看!”
谢渭虽然有三子一女,但除了女儿,他对这三个儿子都不是很满意。
长子谢权习武从军,却武艺平平,缺少韬略,自从担任豹韬卫大将军以来,可以说是祸事不断。
次子谢骏虽然靠着他的扶持当上了工部侍郎,却才能不显,轻谋易动。
幼子谢恪少有才名,自担任大理寺丞后,刚正不阿,为人称道,但因为早些年父子二人之间的芥蒂,已然数年未有往来。
谢渭今年已经七十有四,到他这个年纪,最大的心愿就是后辈儿孙中能有继承家业者,可三个儿子看下来都不成器,反而是他的孙子、谢权之子谢蕃心思灵活,有望成为谢氏一族的柱梁。
见次子这番慌里慌张的模样,谢渭很是不悦,“你慌什么?”
谢骏被父亲一顿训斥,只得低下头来,委屈地不敢说话,谢渭不屑道,“一个没兵权的秦王而已,如果能把执掌天下兵权的梁王拉入我们的阵营之中,那翰儿的太子之位就有十足的把握了!”
谢骏闻言,撅嘴道,“您老难道就指望帮梁王说一次话,他就会加入咱们吗?”
谢渭斜视他一眼道,“当然不可能!”
他扶着楠木桌子缓缓坐下,“我想撮合淑儿与梁王独子宗政元恒的婚事,只要这桩婚事顺利,我就有八成的把握将梁王拉到咱们这一边来,届时太子萧彻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谢骏这才明白父亲的一片苦心,太子萧彻现在之所以还能稳坐东宫,最大的依仗便是梁王宗政长玄的支持,只要能将梁王拉拢过来,就等于除去太子的臂膀,纵是太子还掌握着礼部和刑部,也挡不住谢渭的攻势,毕竟后者掌握着六部中最强有力的户部和吏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谢骏想到这里微微皱眉道,“可是梁王会同意这桩婚事吗?淑儿今年只有十二岁,还有两年才成年,梁王会耐心等这两年吗?”
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梁王会因为一句虚无缥缈的承诺等下去吗?
谢骏没这个信心,毕竟皇帝适龄的公主还有好几个,梁王何必一颗树上吊死呢?
谢渭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的地方。”
“商量什么?”谢骏不解道。
谢渭目光直直地看着他,“我准备先让凝儿嫁过去,稳住梁王,让他知道我们的诚意!”
谢骏脸色一下子变得红胀无比,因为谢凝儿就是他的嫡女!
所谓的先嫁过去,无非就是当妾室,这对十分在乎脸面的谢骏来说简直不可接受!
他气呼呼道,“大哥那里也有好几个女儿,为什么父亲偏偏选中凝儿呢?难道不知道我就这么一个独女吗?”
谢渭知道次子在生闷气,他解释道,“因为她们都是你大哥的妾室所生,上不得台面,为父想来想去,也只有凝儿才能担此重任!”
就在谢渭准备进一步说服次子时,他派去盯梢的随从急匆匆赶了回来,“相爷!”
“什么情况?”谢渭问道。
随从上气不接下气,“相爷,梁王的车驾刚出皇城,立马就拐进了东宫!”
“什么?”谢渭惊讶道。
“小人亲眼所见,梁王的车驾刚驶出皇城,立马就拐进了东宫,没有一丝迟疑!”随从又补充道。
谢渭一时愣在原地。
“父亲!”谢骏看向已然愣住的谢渭轻声呼唤道。
“看来梁王是打算全力支持太子了!”谢渭遗憾道。
东宫。
宗政元恒跟在宗政长玄身后拜见了太子萧彻。
太子萧彻给宗政元恒的第一感觉就是他面相颇为阴柔,眉眼中有一股女子之气。
此人必定行事无所顾忌,出手狠辣非常,宗政元恒心道。
“请!”太子萧彻对宗政长玄颇为客气。
宗政长玄也点了点头,没有客气,临进门时,他回身对宗政元恒道,“你且在东宫里闲玩一会儿,我与太子和太傅有事商量!”
“是!”宗政元恒埋首回道。
太子萧彻见此对一旁的下人小声道,“立马去请公主过来,引梁王世子在我宫中游览一番!”
“诺!”下人立马领命而去。
东宫密室中,一盏微亮,照亮坐在此间的三人。
主位上坐着的是太子萧彻,一改方才的云淡风轻之色,面上似有愁容,左边坐得是梁王宗政长玄,坐在他对面的则是太傅徐勃,头发花白,号称是太子萧彻的军师。
才刚坐下,徐勃便不悦道,“梁王今日在朝堂上颇为不智,竟然让谢权拿走了京畿守备值守一职,要知道京畿守备军八万余人乃是何等强大的一股力量,太子的东宫六军加起来也只有三千余人,如果事由突然,恐怕我等都将是谢氏一族的阶下之囚!”
宗政长玄摇头道,“便是本王不说,陛下也会将此职交到谢氏一族手中,陛下命本王整顿京畿守备军,又命谢渭为监军,就是让他来制衡本王,京畿守备军迟早是要交给谢氏一族的,毕竟在陛下的眼中,本王的威胁比谢氏一族还要大!”
“可恶!”徐勃恼怒道,“也不知谢渭给陛下灌了什么迷魂汤,让陛下如此言听计从!”
宗政长玄抬手道,“徐太傅勿忧,京畿守备军少经战事,战力极弱,又以谢权这种昏碌之人为帅,不足为惧,本王只需千骑便可大破之。”
太子萧彻与太傅徐勃一起抬头,“梁王所言非虚?”
“本王何曾骗过人!”宗政长玄稳操胜券道,“当年江淮流民叛乱,本王只用七百骑便击破三十万流军,这八万京畿守备军本王还不放在眼里!”
说到此处,宗政长玄转头看向太子道,“今日谢渭那老狐狸不知何故竟与我攀附渊源,得知我在为元恒选亲后,最后想将金阳公主嫁给元恒,从而拉拢于我!”
“什么?”太子萧彻霍然起身,惊怒道,“老匹夫安敢欺我!”这分明是在挖他的墙角。
太傅徐勃急忙起身安抚太子坐下,转而问道,“不知梁王作何回答?”
宗政长玄神色不变,轻轻摇头道,“徐太傅应知,本王无法拒绝此事!”
太子萧彻闻言立即变色,刚想起身,徐太傅又立马制止道,“皇家天女下嫁臣子,乃是莫大的荣幸,无故拒婚者以谋反罪诛,此乃我大靖国法,梁王不拒乃是明智之举。”
“为今之计,乃是请太子出面,尽早让陛下赐婚于清河公主于梁王世子!”徐太傅道。
太子萧彻闻言苦恼道,“我之前也探听过父皇的口风,只是父皇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示!”
东宫花园里,水榭廊桥,花红叶绿,美不胜收,宗政元恒几乎以为自己误入仙境之中。
“世兄!”一道清脆的少女声唤道。
宗政元恒蓦然回首,正是当日他在平南侯府所见的清河公主,闺名若雪,年方十六岁,只见她依旧一身金色丝裙,面着薄纱,好似天帝之女,飘然下凡。
“元恒见过公主殿下!”宗政元恒急忙作礼道。
“世兄好生神秘,当日平南侯府中,不显山不露水,仅用三招便击败了皇甫玉龙!”清河公主轻笑道。
面对清河公主的恭维,宗政元恒付之一笑,“当日我也没想要教训他,只是他误以为我跳出来是为了和他争风头,这才起的争端。”
清河公主当日就在平南侯府之中,知道宗政元恒所言属实,她又问道,“世兄这身武艺从何处学来地?好生了得,我父皇曾夸皇甫玉龙的武艺乃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可在你手中竟然连三招也没挨过!”她要是知道方才在校场中,宗政元恒轻松击败六级高手皇甫敬,恐怕会更加吃惊。
宗政元恒知道,清河公主这是在盘问他的底细,他自然不会明说,所幸骗人这种功夫也不难,胡诌便是。
“自我有记忆开始,便居住在一蔽绝世外的山谷之中,山谷之中除了我就只有大师父和二师父二人,他们一个聋,一个哑,生活很是无趣,因此只有日夜不停地练武,才能舒缓我的内心,直到后来父王把我接了出来!”
“难怪如此!”清河公主恍然大悟,原来梁王世子根本就没有丢失,是梁王为了培养他,偷偷把他藏起来了,也难怪宗政元恒的武艺会如此高超,与他相比,皇甫玉龙的努力根本不值一提。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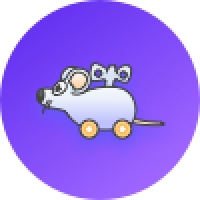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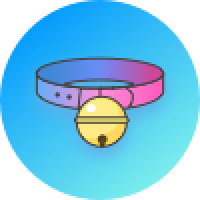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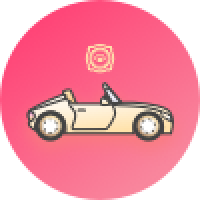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