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智高带着残兵败将继续往大理羊苴咩城进发。过了秀山郡,便是威楚府,沿着礼社江和把边江北上,若是赶得急,几日便可抵达大理。
可是侬智高却发现,他越往北走,就越有些不对劲。
大理地广人稀,他的队伍又为了避免和大理驻军发生冲突,一路潜行匿踪,常在崇山峻岭之中穿行,几日都见不到一个人影。
可越靠近大理府,出现在他身边的人迹就越频繁。
侬智高知道,一直跟在他身后的高升洁人马声势弥盛。
高家在大理朝堂之上,举足轻重,各地驻军当中,也有高家的子弟,高升洁一纸号令,那些手握重兵的守将,谁敢不给高小姐的面子?
高升洁本是出来玩耍的,带的人并不多,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旦等她凝聚到一定实力之后,便会不顾一切的再次发动攻击。
而且,当初盘江之战时,临近特磨,鱼龙混杂,现在里大理不过几百里地,已是高家的地盘。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尽占,侬智高料想着此番若是再与高家接仗,自己定是讨不到半点便宜。
人马走了几日,已是疲惫不堪,侬智高只好下令,在距离威楚府五十里开外的江边暂时扎营休息。
奔波了一路,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心力交瘁,原先约好的杨家人马,并没有准时出现,又令他心急如焚。
在安顿好手下的将士后,遣了几队人马,分成三路,再次入洱海领地,向杨义贞父子讨援。
所有的烦恼,都能用烈酒和身体摩擦的快感来发泄。
侬智高早已没了当初起兵时的豪情壮志,见到宋人风声鹤唳,只能用烈酒来麻痹自己。
喝了酒,他沉重的脑袋便想不了那么多事情,剩下的只是性欲。
再趴到他刚刚争夺过来的弟媳身上去,很快就会进入无我的状态。
虽然那只是短短的一刹那,却能令他感到无比轻松,仿佛心头的所有包袱和担子,全都被卸下了。
刚生过孩子的杨金花,下身满是恶露,可侬智高顾不了那么多,哼哼唧唧地与她纠缠了一阵子后,便把精液射了出去。
紧接着,又笨重地从杨金花身上滚了下来,仰面朝天,大声地喘息着。
“陛下,”守在门口的侍卫隔着大帐的帘子喊道,“范夫人求见!”
“这时候,她来见朕作甚?你赶紧回复,便说朕有要事在忙,有什么事,明日一早再提!”侬智高没有好气地回答道。
自从范叔、范季兄弟二人回兵接应阿侬未果,又在求援的半途让宋军堵回之后,侬智高总觉得这两人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
至于他们两个,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料想也没这么大的胆子敢对他隐瞒事情,唯一的解释,这一切都是范夫人在背后操纵。
这若是换在邕州,他早已拿范夫人问罪了,不弄个明白,绝不轻易罢休。
可现在,他身边别无良将,正是用人之际,若是把范夫人给惹恼了,天知道这个两面三刀的女人,会不会又倒戈到宋人那边去。
所以,他只好暂时忍了。
但忍归忍,一想到范夫人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些愤懑不已。
“可是……”帐外的侍卫有些支支吾吾,“范夫人道,此事关乎大南国兴亡,非要面见陛下才行!”
“罢了!”侬智高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边将袍子披到自己的身上,一边又瞟了一眼失神般躺在床上的杨金花,对帘子外的侍卫道,“你让她到中军大帐议事!”
“是!”
现在的杨金花已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两眼无神,此时就算再多几个人趴到她麻木的身子上去驰骋,想必也不会再有太大的反应。
侬智高叹了口气,杨金花姣好的面容,高贵的出身,俱是他求之若渴的。
然而没想到,自己虽然占有了她,却如同占有了一具尸体一般,令他好不恼火。
本来,在邕州城时,看着穆桂英跪在他的脚下不停求饶,他便相信,再是刚强女子,也会有折弯的一日。
可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容不得他慢慢打开杨金花的心房,让她彻底属于自己。
议事的大帐内,范夫人已经在等着侬智高了。
自从被阿侬剥夺了那身金甲之后,她便换上了自己的铁甲,看上去虽然朴素了一些,可脸上那盛气凌人的神情,却有增无减,仿佛这场战争的唯一胜利者,只有她一人而已。
“夤夜求见,不知所为何事?”侬智高说着,走到主案后头坐下。
“陛下,”范夫人就算再怎么自以为是,在侬智高面前,却还是不敢造次,连忙站了起来。
她就是这么忍过来的,在娅王阿侬面前唯唯诺诺,却在关键时刻,狠狠摆了她一道。
现在面对侬智高,料想亦是如此。
“微臣想与陛下谈谈洱海领主之事。”
侬智高看了她一眼,道:“既是公事,为何不留在明日白天说?”
范夫人不慌不忙,道:“微臣也只是刚刚想到,事体迫在眉睫,扰了陛下兴致,还请恕罪!”
“罢了罢了,”侬智高挥挥手道,“有什么事就赶紧说。朕奔波了一日,已是有些累了,想早些歇息。”
范夫人想了想道:“陛下可曾想过,为何洱海领主迟迟不派兵接应?可知其中道理?”
侬智高的脑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根本不会像从前那般冷静沉着的思考,现在他所念的,一心想尽快进入大理府,寻求庇护。
只有在恢复足够实力的情况下,才能让他重新像以前那样思考。
他摇摇头道:“你倒是说说看!”
范夫人道:“陛下,大南国接连惨败,先是归仁铺,后是特磨,眼下仅有数百之众,即便当真到了洱海领地,那杨家料想也不会另眼看待。”
侬智高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这才发现,自己从前想得太过简单了一些,以为把穆桂英送出去,就能从杨义贞父子那里借到人马。
现在的穆桂英,也不过是一介俘虏而已,这样的礼物,还不足以让洱海倾力相助。
他又问道:“依你之间,朕又当如何?”
范夫人趋近侬智高身边,道:“眼下陛下需做两件事。其一,尽快取得一场和高家战斗的胜利;其二,速速与杨金花完婚!”
“嗯?”侬智高不由地一愣,“战胜高家,自证勇武,这朕自是了解。可与杨金花完婚,却又是为何?”
范夫人道:“陛下请想,杨义贞父子驻足观望,不过是对陛下心存疑虑,怕陛下并非真心归附。若是陛下明媒正娶了杨金花,那穆桂英不就成了陛下岳母了么?到时,陛下将其赠予杨义贞父子,也算结了亲,必能博得那父子二人的信任!”
“这……”侬智高犹豫起来。
把穆桂英送出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而且他也知道,穆桂英到了杨义贞父子的手上,定也捞不到半点名分,下场比那些奴隶还要凄惨。
若真如范夫人所言,那他自己岂不成了贱人的女婿?
这何止是自贬一级啊,简直是变相对杨家父子效忠。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又如何能取得杨义贞父子的信任?
范夫人见他举棋不定,又赶忙道:“陛下,忍辱负重,只是一时,若真能借来洱海之兵,中兴大南国,指日可待。到时候,莫说是洱海领主了,就连大理的皇帝,交趾的郡王,也要忌惮你几分!”
侬智高思忖了良久,最终还是答应了。
是啊,他现在只能这么做,而且距离大理府越来越近,范夫人口中所说的两件事,要越快办妥越好。
试想,谁会对一个肯将自己岳母双手献出的心生疑虑?
范夫人进完言,辞别了侬智高,转身出了大帐。
此时外头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辕门下的火盆,还在滋滋地冒着橘色的火光。
在黑暗里,她不禁牵了牵嘴角,微微地诡笑了起来。
摸着黑,范夫人快步走回自己的帐内。
虽然僮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可妓营的建制仍在。
曾经在她手底下的那些姑娘,都在兵荒马乱之中,投降的投降,走散的走散,被杀的被杀,只剩下三四名女子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穆桂英。
可僮军败得越多,士兵们就越沉迷于女色,有的时候,甚至前来光顾的人比当初在丝苇寨还要多。
与侬智高一样,在无比的失落和挫败感中,唯有肉体摩擦时的无我状态,才能暂时令他们忘掉一切。
比起杨金花来,穆桂英可算是凄惨得多了,每天被那些朝不保夕的僮兵变着法子玩弄。这不,范夫人刚离开了一会儿,她的姿势就又变过了。
穆桂英上身和下身折叠在一起,浮于半空。
没错,她正是离地悬浮着!
原来,在妓营的门口,有一排拴马桩。
这些木桩是僮军扎下营寨之后,刚刚打下去的,本是用来拴住马匹,不使其逃散。
毕竟现在人手不够,也没专门的人来看管马匹,那些逃命逃了一整天的士兵,在休息前,把马往桩子上一栓便了事了。
现在,马桩上栓的却是穆桂英。
她的两个手腕和脚踝上,都被绑了一根拇指般粗细的麻绳。
四根麻绳的另一端,被分别栓在了她左前方和右前方的两根木桩上。
由于扎营匆忙,木桩也是胡乱打的,专挑土质松软的地方,用锤子砸下去了事。
所以在妓营门前的三根木桩,大致呈品字型,而穆桂英就被绑在这品字型的三根木桩中间。
她之所以会悬浮在半空,是因为她的小腹上,还被顶着一根木棍。
木棍约一握粗细,像是从某根折断的枪柄上锯下来的,长也不到两尺。
在木棍的左右两头,各被钻了一个小孔,比起绑在她手脚上稍细的绳子从小孔里穿过,另一端固定在穆桂英身后不到三五大步远的那根木桩上。
横亘的木棍顶在穆桂英的肚子上,将她整个腰身都固定起来。
因此当她手脚上的绳索被收短之后,直到她双脚离地,两身折叠,也依然不能移动分毫。
黑暗中远远地看过来,穆桂英当真就像是漂在半空里一般。
穆桂英柔软的小腹上被顶着木棍,身子又被上下折叠起来,几乎让她透不过气来。
她的脸部几乎能够亲吻到自己的脚尖,臀部却紧紧地向后突起,露出两个可耻的肉洞。
一名身高八尺的壮汉正立在穆桂英的身后,肉棒深深地从后面插进她的小穴里,不停地冲击闯荡。
每一次撞击,都让快要窒息的穆桂英两眼翻白,眼泪鼻涕和口水,一起流了出来。
“啊!穆元帅,你的小穴可真骚啊!老子每天来操你几遍,都觉着不够过瘾呢!哈哈哈哈!”那汉子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紧紧地抓握住穆桂英的臀部,使劲地朝着两边掰了开去。
如此一来,那正在备受蹂躏的肉洞便看得更加清晰。
肉洞在其中一深一浅地抽动着,曾经被缝合过的阴唇里外翻动,针脚留下来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这伤疤难以消除,却能够随着时光推移,渐渐淡化下来,可现在被这汉子一挑弄,穆桂英阴户充血,针脚竟有变得明显起来。
“唔唔……住手……放,放我下来……”穆桂英艰难地摇着头,凄惨地叫喊着。
这样的姿势,让她感觉被绑在刑架上还要难受,只一会儿的工夫,便已是浑身冒汗,变得有如水洗一般。
两端各连着绳子的木棍似乎将她整个人不停地往后拽,可是在她手脚上的麻绳,却又拼命地把她朝着前面拉,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的承受,都已到了极限。
粗糙的麻绳摩擦在她的手腕上脚踝上,将她的皮肤一层层地磨破,泌出血丝来。
这比麻木的下身遭受奸淫更痛苦,她不得不反手握住紧绷的绳子,却依然难以保持身体的平稳。
无处着力的身子,在一次次的撞击下,左右晃动,更增加了她的痛苦。
可是在身后的汉子,却以为穆桂英是在反抗,突然腾出一只大手来,狠狠地按到了穆桂英的后脑上,将她的脸用力地往下按压下去,喝道:“贱人,别乱动!等老子把你操完,后面还有一大帮人呢!”
“呃……”穆桂英闷哼一声,感觉自己的腰身仿佛快要被折断了似的,禁不住一阵酸痛,上身也跟着被按压到了双腿中间去。
她的双手和双脚是被分别绑在前方左右的两支木桩上的,张开着一个巨大的角度。
此刻被那汉子如此蛮横地一按,她的身子便陷入到自己双腿中间去。
“啊……”穆桂英更加难受,痛苦地呻吟不停。
这时,又一位壮汉弯下腰,从绑在穆桂英脚上的绳子下钻过,站到她的跟前来。
一身精赤的肌肉,就像铁打铜铸一般,硬邦邦的。
胯下的肉棒,也和他的体魄无差,坚硬得就像一根铁棍。
“铁棍”昂首向上,硕大的龟头几乎贴到了他的长满绒毛的肚脐眼上。
就在穆桂英被按得脑袋往下俯去时,这根肉棒正好朝上一挺,不偏不倚,插进了她的嘴里。
“哈哈哈!大元帅,你现在的口活真是越来越熟练了,惹得老子心花怒放啊!”这壮汉放肆地大笑着,腰部毫不留情地对准穆桂英的咽喉狠狠插了进去。
一时间,在女元帅的颈部,鼓起了一道粗壮的轨迹,就像体内有一条巨蟒在滑动。
已是双眼翻白的穆桂英,这时更加感觉面前金星乱冒,耳边也嗡嗡地响个不停。
“唔……”穆桂英已经说不出话来,肉棒上刺鼻的骚臭味不停地刺激着她的眼睛和鼻腔,让她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当她的脑袋被面前的士兵接过来捧在手心里的时候,那人为了让自己的肉棒更加深入,便拿双手紧紧箍在她的后脑上,继续使劲地往下压。
另一边,他还踮起了双脚,把巨大的龟头不停地往上顶。
穆桂英感觉火热坚硬的肉棒几乎捅穿了她的整条食道,插进肚子里去。
胃部由于受到刺激,也在抗议地翻滚不停,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拼命地往上涌。
然而,她的喉口已经被堵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在无力地冲击了几下之后,又疲软地退回肚子里去。
既然吐出来,穆桂英拼命地想要把这股浊流咽下去,可被扩撑到极限的咽部,早已丧失了收缩能力,不仅无法吞咽,更是透不过气来。
每当这种时候,她总会有种快要死了的错觉。
事实上,她当初确实在死亡边缘徘徊过一回,只是想到了自己的使命和牵挂,这才又还魂过来。
本以为,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起死回生,定会让她成就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却没想到,反而让她遭受了更加沉重的罪过,仿佛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料想真正的地狱,只怕也不过如此吧?
一前一后的两个士兵,同时往穆桂英毫无抵御能力的嘴里和小穴里抽插着,似乎早已不将她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堆只配供人发泄的烂肉。
在前面和后面的交替捅插下,就连钉在泥地上的木桩也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随时都会连根拔起。
她的体力被迅速地掠过着,反手抓握着麻绳的手也跟着慢慢松弛下来,到最后,已经顾不上皮肉被蹭破的痛楚,由着那两名士兵随意摆布。
摸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士兵们才先后射了出来,当粘稠滚烫的精液汩汩流进她身体的时候,她已经感觉不到羞耻,反而一身轻松,就像得到了解脱。
像扯线傀儡似的控制着她全身的绳子本来被拉得紧紧的,但在士兵们的反复冲撞上,此时变得松弛起来,当两人先后退开,她依然被折叠着的上身就像秋千似的,在半空中慢悠悠地晃荡起来。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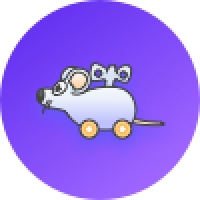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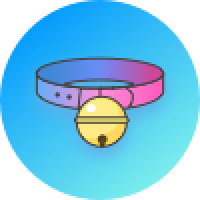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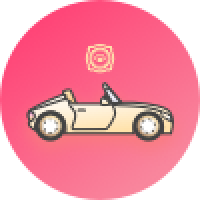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