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兰德常常觉得人活在世上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用功。
年幼的时候,族人处心积虑争夺地位和财富的以身试险是无用功,大一点了,母亲祈盼家人平安的苦苦哀求是无用功,然后,她企图麻痹自己而陷入的长达数月的酩酊大醉是无用功,再后来,叙拉古大家族家长们在她剑下求饶的挣扎是无用功。
当然这个结论拉普兰德不是这个时候得出来的。
她把剑从那个壮硕的叙拉古人胸口抽出来的时候,被带出的粘稠血液滴上了他的徽章。染血的徽章被毫无尊严地扯掉,变成廉价啤酒盖一样的东西被丢在手里抛来抛去。长剑在华贵布料上擦干抹净之后被挎回腰侧,同伴也处理完身上血迹在不远处等她。
拉普兰德就像往常一样在一片被利刃和剑气划得稀碎的残肢断体中笑着扬扬手,把战利品拿给她看。
这是她们的游戏,用仇人的性命做一场平淡无奇的收集。
伤势都是不在意的,只要不影响活动,就由它们自己愈合。疼痛是早已习惯的,她们有别的办法让它自行远去。
可她突然听见德克萨斯说要离开了。
她愣了一下之后还是笑——好啊,那我们去哪?
是我,不是我们。
德克萨斯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淡得像是拉普兰德在做一场荒谬的梦。
梦里的德克萨斯说,她厌恶了杀戮和亡命,仇人已死,她想过回平静的生活。
她还说她戾气太重,根本藏不住身份。
然后她们爆发了第一次不是以撕咬的亲吻和狂暴的进出为结束的争吵。
原因是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她矿石病史无前例的一次发作,近乎癫狂的痛楚从四肢百骸膨胀开来,痛得她都不知道应该捂住哪,最后只能攥住德克萨斯的前襟。汗水一瞬间就流进了眼睛里,又立刻被生理泪水冲出来,也不知道最后糊在了脸上哪个位置,反正她已经连德克萨斯的脸都看不清了。
后来她也曾回想,当时痛的究竟是身体还是心脏。但她也从来没有想下去,因为怎么想都已经是无用功。
德克萨斯也不会回来。
恢复意识的时候拉普兰德已经躺在了她们小屋的床上,手里还攥着德克萨斯的外套。屋子里没有少什么,只是立在墙角的剑只剩下她的。手指已经僵硬酸痛到麻木,她抖着手再次把那件她无数次亲手从德克萨斯身上剥离的布料随手丢在床边的地上,闭上眼等另一双手的撕扯。
她倒是等到了。只不过以前是德克萨斯撕扯她的领口,现在是疼痛撕扯她的心脏。
然后她肆意的放声大笑是无用功,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的泪水也是无用功。
笑声响彻整个残破的屋子,填满她身旁的空间,又在层层叠叠的回音里反反复复地告诉她,这里已经是怎样再无回响的空旷。
她们曾在逼仄的小屋里拥着对方,听着呼吸和心跳协奏的华尔兹起舞,也在互相上药时吻过彼此颤抖的脊背,在叙拉古的雪夜依偎而眠,更多的时候,她们举杯灌下成箱的酒,然后跌跌撞撞不知道究竟醉了什么地抵死缠绵。
痛楚又一次漫上,几乎夺走了她的呼吸。眼前明明是一片黑暗却又好像苍茫的白,拉普兰德恍惚着感觉可能死亡大概就是这样。
虽然终究她还是醒了过来。
那个时候拉普兰德就开始笃信,人活着实在是一场无用功。因为死去毕竟万事空。而所有人都是迟早要死的。
她在叙拉古又游荡了一段时间,后来听闻了德克萨斯加入了一个有关感染者的组织,于是她也不顾千里,凭借强盛的力量和严重的病症留在了那艘舰船。
战争,厮杀,屠戮,收剑。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结束打斗之后,德克萨斯会看向那个代号能天使,笑起来甜美得像她做的苹果派一样的萨科塔女孩,而不再是跟她一起走回两人的小屋。
拉普兰德就摸摸刺破脸颊的黑色晶石,笑一笑然后转身跟上返程的队伍,医疗干员叮嘱她的注意事项都成了无用功。
既然死亡是迟早的事,那活着的时候何必自寻烦恼。
虽然她也没想过会来得这么快。
前一天晚上,拉普兰德在罗德岛其他干员的闲聊里听说德克萨斯以为,总有一天她的过去会追上她。
小白狼抖抖耳朵,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德克萨斯,那都是无用功了。
然后又眯了眼,晃晃的尾巴告诉她,她其实忍不住地,在开心。
追上吗?
既然德克萨斯这么说的话……拉普兰德又开始觉得,病症与结晶对她身体的侵占,也是无用功。
她总能追上的。
落单的狼当然会用性命去追逐唯一的同伴。
拉普兰德不怕犯错,毕竟这世上也很难说有什么真正是对。不过她没想到,她会犯一次以为自己就是德克萨斯的过去的错。
叙拉古的人居然来了龙门,可见如今究竟在怎样没落。又没准她离开之后各大势力重新洗牌,现在更强盛了也说不定?
拉普兰德猛然发现原来她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乡。
可是现在不是思乡的时候,刚与整合运动结束一场苦战的罗德岛遭遇了黑手党的袭击,枪械的轰鸣里她看到德克萨斯接连把手里的剑全都扔出,捅穿高台上红发萨科塔背后的黑影,潮水般涌来的敌人面前所有人都自顾不暇,尤其是德克萨斯显然是那群人真正的目标。然后她别无选择,两柄剑护不住两个人四面八方,体力耗尽左支右绌,余光看到霰弹铳的瞬间,只来得及把德克萨斯按进一人深的掩体。
冲击过后拉普兰德试着动了动,估摸着肋骨断了个七七八八,和弹头的碎片一起解剖了她大部分的内脏。
庆幸了一下还好没被打穿脑子或喉咙,还能和难得又灰头土脸的小灰狼再说几句话。
“德克萨斯……”就算说来无用,但毕竟……还是要说。
“…你……那时候…真好看……”浅灰的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金瞳,眼神有一点涣散,像有星子无意轻闪的叙拉古晴朗夜空,仿佛透过她在看向远处,可她又实实在在是对着她说话。
“…现在也好看……”
“更好看……”
“…可是那时候……”大股的血水混着白狼的喘息从她獠牙之间泄出,她自觉是呛着了,可是也没了力气咳嗽,只是颤了颤胸口。
德克萨斯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她杀了那么多人,她们一起杀了那么多人,她们都清楚现在的情况医疗已经是无用功。可她见不得这样,她德克萨斯竟然见不得拉普兰德成为她眼前的第无数个将死之人,于是她下意识地说了点什么想终止她的遗嘱。
可她在看到拉普兰德露出一个近乎惨烈的笑之后才意识到,她又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闭嘴。
可是解释和挽回也成了无用功。
拉普兰德眼里的星点终于彻底黯淡下去,她还是笑着,虽然喉咙已经被血沫糊得嘶哑,也让德克萨斯听到了最后的话。
“…那时候……”
“……你爱我啊。”
她低头的瞬间天光大亮,龙门的阳光像叙拉古的夏日一样,洒满了遗忘。关于家族的覆灭,木屋的烟火,摇晃的货车和一只灰狼手握双剑的屠杀。
罗德岛的干员休息室恢复了寂静。这一次,德克萨斯明白了,大笑和泪水,全是无用功。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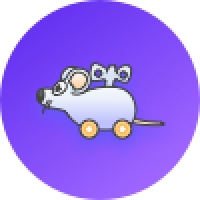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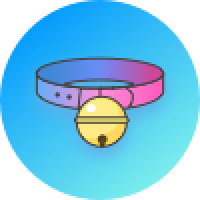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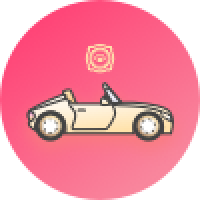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