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博令无差,有互攻,注意避雷
*因为朋友喜欢令姐姐故摸之,以及因此本文博为她岛博,与我岛博无关
“昨夜我梦见了你,”令带着酒后的慵懒,把这句话递给重新将眉目与表情都掩进兜帽里的人,仍氲着些许醉意的眼捕捉到对方一瞬的僵硬。她性情算不上恶劣,但许是近几日受妹妹们耳濡目染,对眼前人也忽然起了撩逗之心,便微微拖着嗓子,顿挫道:
“不!兴许是你梦到了我。”
也许彼此入梦的形容过于暧昧,被面罩遮住眼神的人轻咳一声,应她:
“庄生晓梦迷蝴蝶?”
透过遮挡的音色听上去多了好些沉闷,还有点哑,但她的顾左右言他使令的笑意进了眼底,嘴上却丁点也不饶过:
“唔,记不得了?”
“可惜,那般得意,却不能与人同享。”
长长尾音拖得好像真的带了孤独叹息,而言语之间日光下澈,山间雾霭散得通透,崖边亭下拢的最后一点晦暗也驱得干净。静到连飞鸟的啼鸣都消弭的距离间,身边人的呼吸将欲言又止在唇边咬了几个来回都暴露得清清楚楚,最后还是清晰又含糊地答了:
“能。”
随后像是为了截住令的追问,她开始语气沉痛地喋喋不休。
“快别说得意了”
“你知道我被得意炸得有多惨吗”
“夕画的”
“没有说夕画的不好的意思”
“虽然但是”
“不只是得意,还有遮目,自在”
“我头都被捶爆了”
“家也被冲没了”
“夕,画得很好,下次别画了”
“至少别再画这些了”
“画了也别放出来打我了”
令在她装模作样的抱怨里爽朗地笑出声,飞扬的眼角眉梢都是清秀又凌冽的意气,浸在灿烂的日曜里,仿佛龙孤身在天地间荡出一片云销雨霁,将这片大地积压在博士肩头的苦难都冲淡了些。
人常好说少年意气,因年少心无所系,未经世事,未染凡俗,所以年轻气盛,是一种空白的锐气。可令已在人间游历了千万年,她见识过,也牵绊着,却还是保有着纯粹的洒脱,而让那份快意更显澄澈。
她没有拆穿博士信口雌黄的胡诌,分明夕说过被罗德岛水枪滋到笔锋都散了的话,却顺着博士的话茬:
“好好,我会同夕说,让她不要欺负你。”
揶揄的话竟被她的坦率笑意裹得显出了宠溺,像是年长者与生俱来的温和与包容,博士的脑海中因这种纵容而浮现出前夜的酒后妄为。
酒自是令请的,不过显然她没有预料到博士如此浅量。金黄透亮的酒液三两盏,对令来说不过是刚刚沾湿了双唇的量,却已经要让博士为她的放纵与不知深浅付出代价。尽管语言系统与逻辑思维并没有停止工作,但对着一个写诗的酒鬼一本正经讲述临床医学的典型案例八成不是一个清醒的指挥官会做的事。
起初令看她坐姿端正,表情平静,还当这只是学者的特别之处,但当她酒意正酣,起身即兴随月影起舞时,博士抚案观摩着她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身姿,兴致起处,竟也不由自主起身,似欲与她共舞此刻的恣意。然而她甚至没来得及站稳,就两眼一花,差点仰面栽了个跟头。
还好,她栽进的是带着酒香的臂弯。
刚刚还宛如云中潜行,身影飘忽遥远的龙,如拨云见月般乍然折返她的身边,状若醉意深深摇晃跃动间阖上的双目,此刻近在咫尺注视着她,竟清明得仿佛那半壶的酒全是入了博士之口。已然被酒劲冲得晕晕乎乎的博士,晕晕乎乎就要将这不着边际的假想当真。她晕晕乎乎地想,若不是令的酒全醉在了她身上,那为什么她现下几乎脚不挨地,却还能如愿仰头吻上令那惹人垂涎的双唇,而未曾被清醒的那个人躲开呢。
博士不是没见过喝醉了酒的人,她向来知道,酒后的人身上会有浑浊酒气,不大好闻,至少她并不喜欢。但令身上全然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气息,反而是一种清冽而馥郁的酒香,随着呼吸一点一点覆盖过来,渐浓后慢慢变得温和醇厚,像一个甘甜暖软的梦。
博士就这样沉溺了进去。她主动探出舌尖,有些莽撞地闯进了酒香的来源。
但让她“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是,贸然的冲锋既没有受到丝毫的抵抗,也没有遭遇任何伏兵,宽容的东道主没有责怪她的无礼,反而相当热情友好地对她的冒犯回以周到的招待。
可惜,长者的好意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宽容被这大尾巴狼理解为纵容,她毫不悔改,甚至变本加厉,熟悉后毫不客气地反客为主,仗着自己“醉酒”,摇摇晃晃地带着龙栽倒在亭中低矮却宽大到可以躺下两人的石案上。
令在仰倒时还不忘探手把案上余的半盏酒捞起,一手护着博士的后脑,一边仰头将酒液含入口中。月光下博士被她垂眼时泛红的眼角蛊到,不安分地爬起来又去撷那被酒沾湿的唇瓣,交缠中又被渡了小半口酒。
也不知醉人的到底是月色还是美酒,博士摇摇头赶走脑子里莫名其妙拐弯抹角的句子,清楚又明白地告诉自己,让她沉醉的,是眼前的人。
纵容她的无赖逾矩,回应她的放肆索取,配合她的贪婪占有,甚至,在她不知满足地展露出她的一肚子坏水儿,顶着湿/热/甬/道里的弱点凑在令耳边叫她“姐姐”时,也如她所愿地下意识绞紧了软肉,面上一瞬的茫然不知是源于错愕还是短暂的双眼失神。
过于得意忘形,以至于博士胆敢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趁龙仍携着喘/息的时候,就又凑上去明知故问:
“姐姐——我是乖小孩吗?”
故作乖巧的语气里又没掩饰好笑意,最终为狼子野心招致了灭顶之灾。
宽宏的龙终于显露她的威压,仅是一个稍稍褪去温和的眼风,就使恃宠而骄的人意识到她的轻率。
然而事已至此,龙不会再给她多余的机会挣扎。从令右手手套外一直缠绕到小臂的绑带,随着她轻声的一个呼哨化为条悠游的小龙,它不需要旁的命令便明白主人的意图,灵活迅捷地盘上博士的双手手腕,成为优雅而坚韧的束缚。
博士来不及惊异这生物的奇妙,就被摁在了石案上,唇舌的纠缠从品尝变成了被品尝。
实际上刚刚的肆意妄为已经消耗了她本就薄弱的体力,酒后的脱力和眩晕更是雪上加霜,使她只能束手就擒,成为龙的盛飨。
衣物遮蔽腰腹的部分被随手剥离,却又被由着袖口牵制,松松垮垮仍半挂在身上。解开的外套潦草铺在身下,双腿被龙尾缠着分开到极致,腰被高高抬起,令摘了手套的小臂与年和夕一样有着延伸至手肘的色彩与纹路,博士的视线下意识地追着那抹绮丽的靛青,却也因此仔仔细细看见令的手指顶进自己的身体。
身下陌生的酥麻感让她无能为力地软了腰,使不上力气却又无法控制地紧绷,从腰到腿的肌肉全都不堪重负地哀嚎着,然而落入龙的眼里则是可爱到令她无法罢休的浑身颤抖。
被她的反应取悦,令柔和了眉眼亲吻她的侧颈,又忍不住贴在她颊边将揶揄的话以呼吸般轻柔的句子递至她的耳廓。
“抖什么?”
博士听到自己嘴硬的“没有”里都带了颤声,干脆抿了唇,将脸埋进自己手臂,眼不见为净。
令看似默许了她的鸵鸟行为,只是捣弄软肉的手指更加勤恳,又深又重的顶撞逐渐逼出在极力压抑下像带了哭腔的轻吟。
愈发猛烈的攻势下,博士招架不住,献出罕有的软糯音声和丰沛汁水意欲求和,然而尝到甜头的恣意的龙却不会就此收手,她顺从自己的意愿,乘胜追击,一如追剿穷寇般意气风发地,将身下人的甘甜掠夺殆尽。
直到那本就稍显低沉的声音彻底沙哑,夜半的钟声与三更的鼓都息了声,令才由着已经瘫软到抬不起手的博士与自己一同睡去。
这一梦酣沉,令醒来时天已破晓。博士竟是先她一步梦醒,穿戴整齐后狗模人样地和她满嘴跑火车。
山岚的消散一并带走酒意的昏沉,令心情大好地顺着博士胡说。
话语随时间更迭,自古便真真假假,如镜花水月做不得数,又何须在意。
而前夜酒事,纵情快意酣畅淋漓,是梦是醒又有何妨。
令拎着酒葫芦离开小亭时看到昨夜她用尾巴写在柱上的句子:
“人间已醉万年,还不许我大梦一场?”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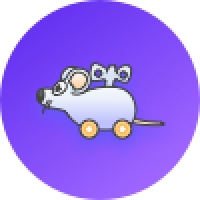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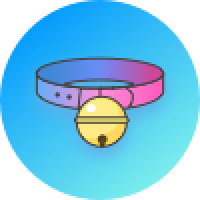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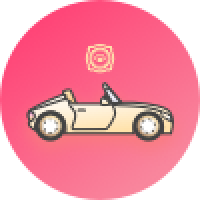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